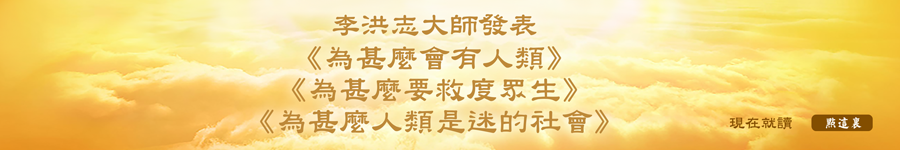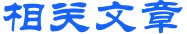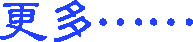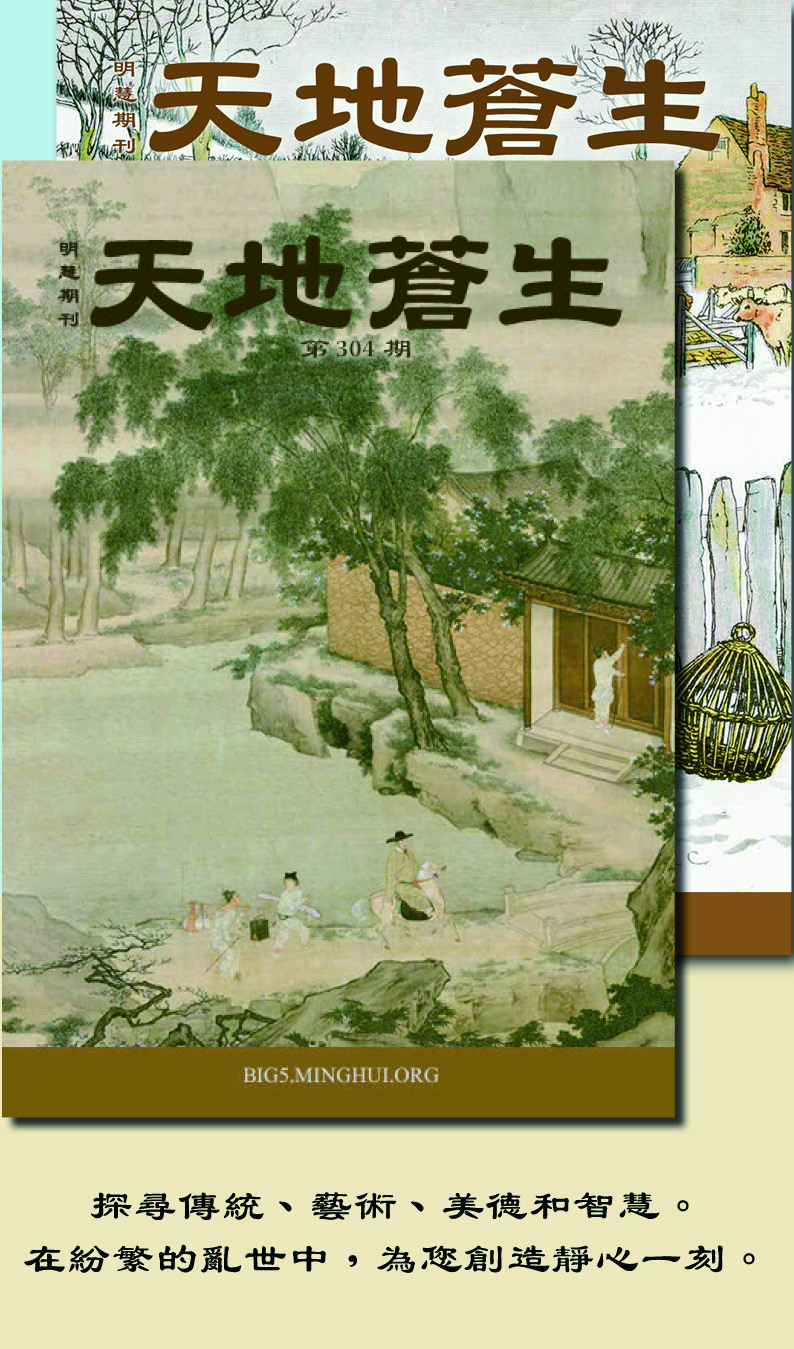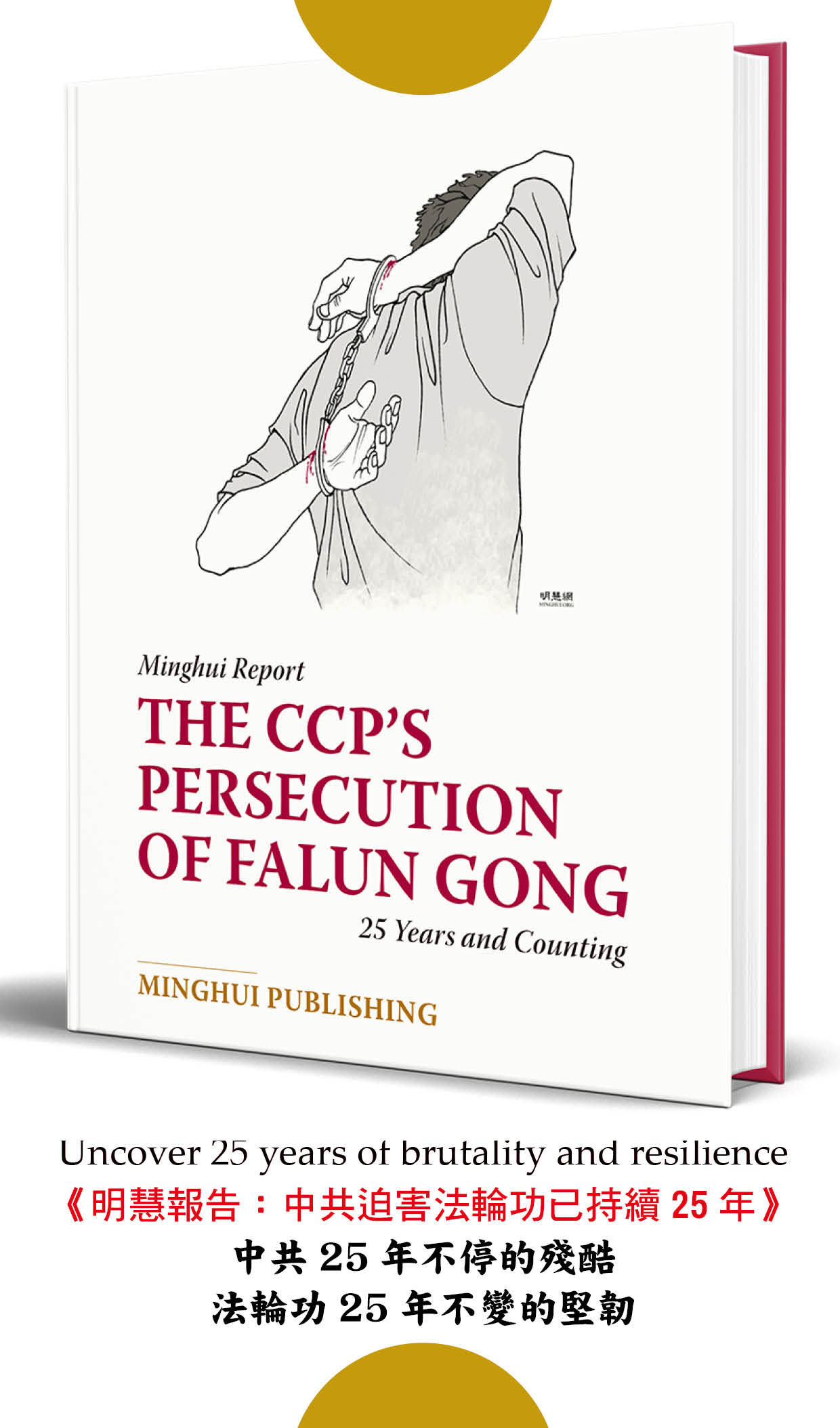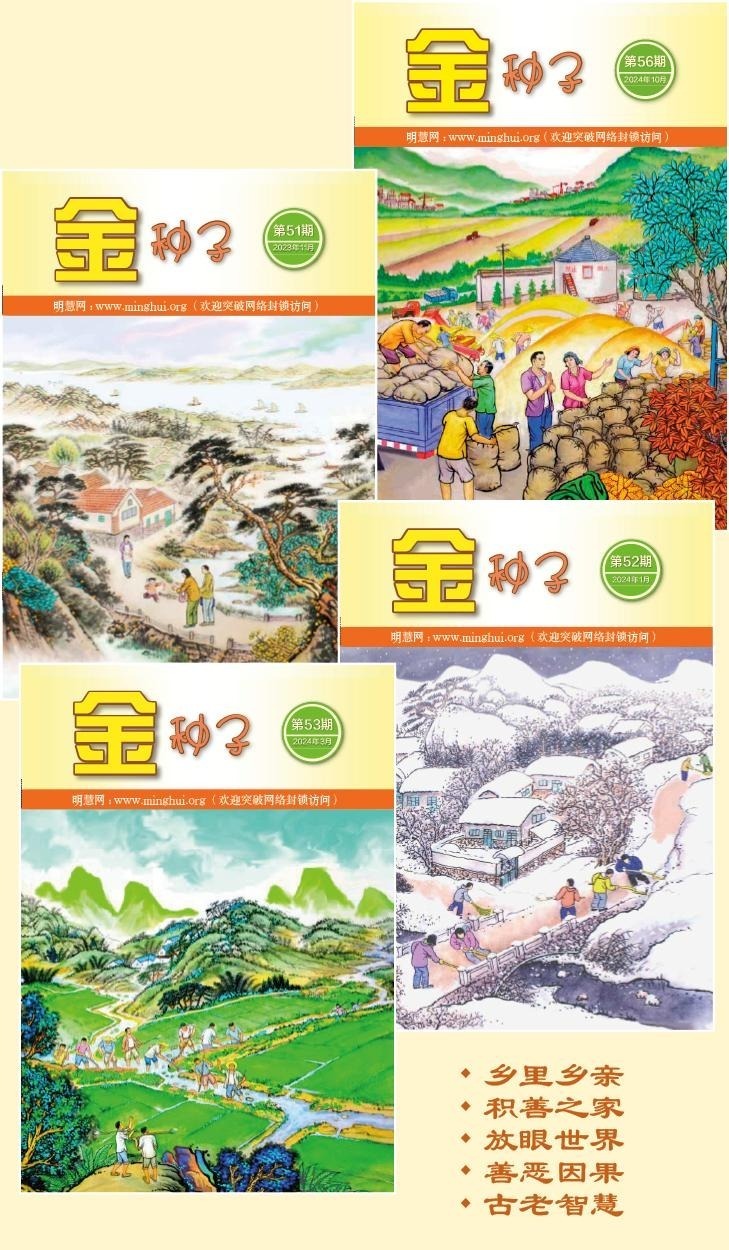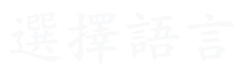因坚持信仰 六年被停发工资
我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食品公司肉联厂职工,65年参加工作,先在饭店后又调旅馆工作,由于神经衰弱,经常失眠,人精神也不好,后来就调食品公司肉联厂当保管员。1992年我突然得病住院,检查说甲肝,经常住院不见好,丈夫是厂长,工作又繁忙,没人照顾,就哥嫂照顾我,但是再治都不好,吃药不起作用,又引起全身得疾病,口腔溃烂,气管炎,鼻炎引起说话都困难,眼睛又是散光近视,看东西模糊不清,乳房又是瘤子,子宫也长瘤子,后开刀,又是风湿,肝脏久治不好,到成都检查胆结石,吃药石头打落了,病还是不好,最后检查是丙肝,医生也说吃药也不起作用,家里只好请保姆。吃药不行那就求神拜佛,算命、烧香、烧纸还是不行,家里亲人朋友操碎了心,自己难受到了极点,没办法,提前退休休养。
在我绝望之时,也就是在1997年3月我喜得大法,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从此以后我走上了修炼之路。这本书使我明白了很多很多,一改以前恶习,真正的在改变自己。以前脾气不好,骂人,重名利,遇事不让人,伤了别人还以为自己有本事,别人怕我,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修炼以后我明白了,我错了,决心改正自己,是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我庆幸法轮功给我带来巨大幸福和美好之时,江××对法轮功实行迫害,诽谤、攻击铺天盖地,把我们修炼环境也破坏了,不能学法炼功。我想不通,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哪错了?修炼大法是我的选择,我不放弃,因为我懂得做人的真正意义,是我的个人信仰,自由,我应该到北京上访,反映我们并不是电视上所诽谤的那样,我们是修炼是在做好人,我决定到北京上访。
在2000年过中国年后,我在天安门金水桥打出了“法轮常转,佛法无边”的横幅,站在那里我的心是那样的平静,祥和。大概两分钟就被警察绑架抓走了,抓到天安门派出所,带上二楼给拍了照,接着就是又打又骂,用《转法轮》书打我头、脸,打够了又罚跪1个多小时。最后把我和其他功友关在一起,个个都折磨的不像样,我看贵阳市一个姑娘昏迷过去了,一个老太太由于反背戴着铐根本不能解便,是我帮忙她解了小便。一直到晚上广元办事处才把我接走,第二天一早我正念走出办事处。
2月份我和其他8个功友又第二次到天安门,刚走到广场中心,就被便衣警察把我们挡住了,他当时打电话就来车子把我们绑架走了,又被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晚上广元办事处的人把我们带到办事处,当晚坐火车到广元一路上都有人押送。
一下车就看见苍溪公安局来了很多人,开了一个大旧车和一个小车,当时给我们录了相,每个公安人员还背了枪,把每个人用手铐铐起,又绑架回苍溪。另外在苍溪还抓了几个功友,一共十多个人,关押在苍溪看守所,钱被搜了,是公安局搜的。看守所开了个理发店,每人剪头收15元,给我们买来东西管你要不要,而且价格很贵,伙食稀饭是短面渣煮溶了的,因他们办了个干面厂,落下来的短面渣给我们煮了吃。
我们被关在道子里,黑不见天日,刚进去把我们单个分开,我、李光清、罗长华三人被劳教一年半,寇志秀被判一年,结果寇志秀在劳教所多坐了半年。判决下来我也不签字,因我没有罪,还把我绑上大卡车挂个牌子,游街示众,我们是在做好人,强身健体,他们强行给我们定罪,上诉不起作用,还是送劳教,其他功友被罚款7千至1万元才放回家。
2000年6月10号左右我被送资中劳教所,进去就是搜身,几个民管会的强行搜身,当时我带有《转法轮》的手抄本,是我在看守所抄的,我拿着《转法轮》不放,几个人强行抢,衣服也被扯破了,书也被他们抢走了,功友李光清为了保护这本书,被他们一顿拳打脚踢,还用绳子捆在树上。
我记得是6月17号成立的所谓“法轮功中队”,七中队,大概有100多人,每天早上6点集合报数,我们全体就打坐炼功。她们就派来民管人员(吸毒的)和男警察把我们包围在当中,男警察带头,手拿警棍,我们一炼功他们就冲进来拉的拉,打的打,铐的铐,拖的拖,有的抓进办公室用电棍打,有的用电警棍烧脸,有的就拖进一间房间里铐在窗子上悬起。
我的衣服被拖烂了,李凤其被打的血肉模糊,多处伤痕,是用钢筋和一把竹块打的,是脱了裤子打的,大家看了都难过,中午很多功友饭都没吃。我们又晚上炼功,民管会发现后又把我们拖出来面壁几个小时到天亮,有的被罚做下蹲,我被罚了一百次,毛坤被罚了一千次,田功友被罚了一千五百次,要接连不断的做,双手抱头,一上一下接连不断的做。毛坤的裤子蹲烂了碗大一个洞,我看见她几天走路都很困难。
有一次因炼功,罗小玉他们整个监室被罚面壁,坐军姿。为了强行转化,把我们不转化的关在监室外坐军姿,不准动,不准洗澡,不准喝水,解手都在监室,民管会轮班守着,给我们读白皮书,我们不听就背经文。由于几天不洗澡,又是大热天,有的功友身上又长了疮,身上也臭,结果好不容易给了一次机会叫洗澡,只给五分钟,澡没洗完,手没解成,衣服也没洗,又被关回监室。
关了二十多天后,又强迫我们在下面操场坐军姿,相互不准说话,两手平放大腿上,两眼平视前方,腰直额正,不准晃动,不准闭眼,每天早上6点坐到晚上11点,臀部象针扎一样,都不敢动一下,不然招来的是毒打。就这样春夏秋冬坐着,天气热,加上很多功友又长疮,满身都有是密密麻麻一片一片的,痒的难受,无法形容,晚上痒的睡不着,这个疮就长了一年多,有的看了都害怕,饭都不想吃。
我洗澡衣服一脱满身是疮,民管会的李某某看了都哭,加之身体里面那个难受是难以言表,就这样艰难的过着。上厕所民管会要搜身,厕所在二楼,一路上民管会站满了的,解手都看着,手纸是统一发,把我们每个人的纸收去,解手再发,解完手又搜身。
开会上课,有个姓张的功友,他不配合不参加会,每天被铐在树上。她说我只听师父的,我主意识要强,我不听你们诽谤大法的话。她被铐了几个月,我走时她又被转入8中队。8中队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才成立的,当时抓了很多学员。我想不管你们怎么迫害,我就坚定背师父的经文。
走正步,跑步,稍微走不好,就被打,就被罚,罗支玉跑不动被罚跑20圈,跑不动民管会拖着跑。有一次罗支玉头被李小林打了一个洞,鲜血直流,把罗支玉拖出去包扎好了,仍不放过,过了两天罗支玉就被“转化”了。因为天热时间又长而且每天规定只能解两次手,每次三分钟,臀部不断蹲的难受,就这样还是有功友被他们拖出去不是打就是铐,他们残酷的折磨着,我们就这样分分秒秒被煎熬着。然而这一切的折磨动不了我们的心,我们平静祥和静静的坐着,默默的背着经文。
在2001年7月中旬,国家司法部带来了马三家的人来劳教所转化我们,李坤容叫了些功友去听,我不去,就叫我坐军姿晒太阳,民管会几个吸毒的人把我叫进洗漱室,说我不去听,他们就猛打我脸,几个功友都被他们打了。去的功友当场揭露他们;司法部的人又把我和功友一共十多个人叫去,一个个的问,我说我们是在做好人,强身健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是不会被转化的。
为了转化我们,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找那些转化了的和帮教围攻,他们中午睡觉叫我们坐军姿。每隔七天半月就开一次揭批会,功友们都不听,有的功友背经文,有的炼功,有的就喊:你们诽谤大法有罪,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们在做好人。民管干部冲进去又抓又打,有的功友被反铐着。他们还搞什么万人签字,就是一块红布往上面签名字,放诽谤大法的磁带,放轻音乐干扰,或是强行做体操,唱歌,千方百计变花样想强行转化我们,折磨我们。
四川省电视台来拍录像,她们提前就准备好了,找几个转化了的说假话,说干部关心我们象妈妈,象医生,诽谤大法欺骗毒害群众。
2001年丈夫来看我,买来我爱吃的东西来见我,结果干部不让见,买的东西让干部收了,没给我;丈夫只好留下一千元钱,悲伤的离去了。那么远的路,天气又寒冷,丈夫年龄又大了,又是过年,别人一家团团圆圆,快快乐乐欢聚在一起的时候,而我却被无辜抓去坐牢,丈夫悲伤地到处托人想把我找回家。
是谁迫害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坐牢?是江泽民!是中共!我仅仅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江泽民利用它手中的权力无端的迫害。
在楠木寺被残酷折磨1年多后,我于2001年8月终于回家了。回家后生活成了困难,因为工资被停发了,我到610找他们给我发工资,我们是在做好人,没有错。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你写个转化书,我们就发。我想,我饿死当讨饭的我也决不写,就这样一直没有给我发工资。直到今年2月我从劳教队回来,从2月份开始发,六年没发工资,该调级没调,每月少领100多元,现在每月只发323元。
回家后我到处讲真相,走好师父安排的路。2001年12月12日我和功友何秀珍到龙山讲真相,我给一个学生发了几份真相资料,被老师发现后硬要学生说是哪来的,不然就开除学籍,学生只好说了。当晚我们住在何功友家没走,第二天龙山派出所就把我们抓了。
在派出所,我不配合,一律拒绝回答,他们就把我们强行抓上车,我不上车、我喊,要那些世人相信大法,不要相信电视宣传,相信大法好,我们是在做好人。
他们把我们硬抓上车,绑架到苍溪县看守所,公安局提审我一律不回答,我想我不应该坐牢,我应该回去,我还要出去讲真相,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走。在看守所给犯人讲真相,进来了我都讲,愿意学的我就教。当时关在一起的有东青的黄群,还有一个赵某某,是回来探亲在歧坪发真相资料被抓,警察把她探亲的几千元钱和买的东西都被搜走了;还有一位姓任,30几岁是个杂犯,我们给她讲真相使她走上修炼之路。
在看守所我们坚持学法、炼功,被发现后,何所长就把我和赵功友铐起,给我们带上脚镣手铐,我们把脚镣手铐取了又炼。在集体学法时被李指导发现,要我们交出来,我们都不交,他就把床铺全翻了,拿电棍子猛打,何秀珍、任某某被打的伤痕有碗口大、紫黑块浑身都是,20几天才好。
隔壁同修李熔是南充市的,来苍溪讲真相被抓,她绝食要走出去。有一天她走出看守所大门被干部发现抓回来,又打又骂,后被南充接走。黄群被判劳教1年多,那天很早,郑所长带了几个杂犯,硬行要送黄群走,我们几个不让抓走,结果郑所长几个强行抓走,把黄群绑架到了劳教所。黄群从劳教所回来后,又去发资料、又被抓,又被劳教、现仍在劳教所。
我被她们抓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我一路发正念,在法院大门台阶上武警把我的头往下按,我不低头,我给他们说我们是在做好人。这次我又判2年劳改。在法庭上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把师父的像和资料说是罪证,我说那是我师父的像,你们给我保管好,以后我会找你们要的。
两年劳改送雅安,车开到成都休息时,郑所长找地方想把我寄放一下,第二天再走,因为第二天才能到雅安。当时车上有几个人,我趁他们不注意正念走脱成功。后来走亲戚住了1月多,仍然到处讲真相,又到遂宁儿子家住了不到10天,又被抓了,儿子和我同时被抓,又绑架到苍溪县看守所,回来后才知道妹夫也被抓,并罚了1万元钱才放人。这是我不注意安全,而给亲人带来的损失。
在看守所遭到了残酷折磨,死囚床上睡了57天,脚镣手铐绷成大字型,手铐是用布裹紧了的,不准下床,不准洗澡,吃饭解手在床上,几天解不出大便,我要求放下来,他们不放,最后在我一再要求下,才放来;用一个盆子,手上一边一副铐子,两个小伙子绷起叫我解,解完后马上又铐起;大热天不洗澡,又痛又痒,手又肿起,右手大拇指麻木了。同监室的李福兰和小马想办法把我衣服扯破了,才脱下来,给我把澡擦了。李福兰看我被折磨的太惨,她就对天又哭又喊,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人家当好人又没干坏事,太不公了。小马吓坏了,要求早点走,不想看到这样的惨状。
我要求何所长放我下来,我说死囚犯还三天两天活动一下呢,还放风,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他说:跑个杀人犯可以,你就不行,你写不炼功,我就放你。我不写,他说一直要铐到我到劳改队才放,他亲自专车送我。我就一直被铐了57天,走的前几天,晚上睡觉还把我和李福兰铐在一起,怕我炼功。
虽然他们这么折磨我,我每天坚持背经文和《转法轮》第一讲。两个月后,何所长把我脚镣手铐铐在吉普车坐垫背上,送到了简阳养马河四川省女子监狱,当时送我的还有女警察马玉春。
到了监狱被分到二监区,2监是恶党的“先进监区”,是那里的重点监区,任务重,相当苦。吃晚饭时一个女犯给我说,这里不遵守监规,要被捆蚕丝兔,她说她捆了以后半年不能端碗,要小心。
刚进监狱,每天10多个小时劳动,每天规定很重的任务,水不敢喝,怕水喝多了完不成任务,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11点,经常加班加点。二监区是加工鞋帮,我是普工,2台机器,忙的不可开交。在看守所折磨的手脚没好,行动不方便,吃饭只有那么10来分钟,特别是早上,去迟一会,饭就被倒了,有时饭没吃完,就打铃集合。
每月一次批斗会,捆蚕丝兔,栽种子,象农民栽秧,捆蚕丝兔,就把象电灯用的花线一样粗的麻线用水泡了,把手反背捆起来,那是很难受的。这样学法炼功就成了问题,我就利用走路背,晚上回监室再晚也背,我不能忘了大法,我就这样坚持着。那时我眼睛难受,身上也难受,眼睛睁不起,有时自己背啥不知道。
当时我总觉得没做对,后来看到经文《路》我明白了,我是修炼人,我只能按师父讲的做,我走出来是证实大法的,不是来劳改的,我应该走出来,于是我开始炼功。我一进来就是严管,被包夹了的,她们报告了罗队长,把我关进了小间一个礼拜。小间就是一个人关一间,里面有一个水泥台,是睡觉的,被盖晚上收监抱来,早上6点抱走,不准洗脸,不准喝水,不给肉吃,饭比平时少一半。
我们坚持学法炼功,回监区我还是炼功,罗队长硬把我留在打扣机那个地方,两台机器,噪声很大,想干扰我。我便想干扰不了我,照样炼,她们就把我拖来拖去,有时就铐起,有时找监护把我守住,不准炼。我始终坚持要背法炼功,她们就把我又转到九监区,两个杂犯包夹,不准和任何人接触,不准炼功,白天晚上轮班守,我就在集合站队时炼功,抱轮,被包夹拉开,不能讲真相,那就喊,趁不注意,洗碗时边走边喊,我想哪怕一分钟都可以。我不报数,他们又把我又关小间。有一次坐了十多天,白天晚上铐起,反铐,冬天被盖又薄,盖一半露一半,靠墙坐着,把被盖横起,下半身盖不了,手反铐坐着睡,被盖会下滑,用嘴把被盖边咬住。我想这不是办法,开始绝食,绝了两天,干部来问我,我说铐起无法睡觉,干部就让解开了,我又可以学法炼功了。回监区后,白天晚上戴手铐,有时铐在床上,还两个人值班看着。来人参观时我就讲大法好,监区放诽谤大法录相,我就喊:不要相信,相信佛法生命有救。就这样我又被关了几次小间。
他们找了几个邪悟了的来帮教,我说:你们说的我不听,你们在乱说,在破坏,我们走出来是讲真相,证实大法,你们是邪悟,我才不听。他们说只要转化了就留在九监区,九监区要宽松些,转化了的一般不参加劳动,看书、打太极、跳舞。我说我也不图舒服。她们看动不了我,把我又送回二监区。
回二监区后,我不参加劳动,不集合,不报数,不穿囚服,我要炼功,不背监规,不做作业,不打报告词,我不是罪犯,我是证实大法的。还有同修罗秀梅,闫会,我们三个都不集合、报数,不穿囚服,集合一完,我们就盘腿打坐炼功,干部就叫来几个杂犯,又拖又拉。我想你们拖不动,我金刚不动。他们就在地上把我拖来拖去。
第二天,我们仍打坐炼功,被罗队长叫来一伙人把我从监区拖到车间,衣服被拖了碗大一个洞,在车间我也炼,在监区我仍要炼,在监区每天早饭前炼功,有时可以炼十多分钟。
这样我坚持了几个月,又被干部发现,就派王雪艳,陈彬包夹,给她们加分,她们两个不准我炼,我打坐时,陈彬把我拖了好远,用她的腿把我腿按倒,我不能动,早上又炼不成,我想哪个地方能炼我就炼,车间炼她们拖,那我就在坝子炼。坝子炼不成,早上炼不成,我想再难我也应该坚持下去,哪怕一分钟两分钟,我要证实大法。
有一次,从车间到坝子又从外面坝子把我拉回车间,这样那天我就进去十几次,还有一次在二楼过道炼功抱轮被唐队长说了我,李管教被扣了当月奖金,热天晚上炼功,监护一晚上来了八次,我起来八次炼功,第二天早上起来五次,我一直坚持着,有时能多炼,有时就炼的少。
因为我炼功,经常被关小间,后来恶管教又采取我炼功扣全监室分,因为扣他们的分会影响减刑。有一次我炼功被发现,恶管教罚包夹徐珊走一下午正步。我再炼,就被铐在大铁门上,铐几次铐不上就把王小华叫来硬往上抱,象捆十字架,又上背铐,脚趾尖沾地,手脚马上肿得像馒头,肚子里那个难受,心也难受。罗队长、许管教就这样折磨我们。闫会象这样被铐过,闫会喊就往嘴里塞毛巾。我和罗秀梅炼功,我们两个被铐在晒衣服的院子。因为来人参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监区来人参观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向他们讲真相,在几千人的减刑大会上,喊“相信佛法生命有救”,我被包夹拉下,又坐小间6天,后来再来人参观,他们就把我转到其它监区看管起来。
管教给我们强行洗脑转化,狱部成了转化帮教组,几个被转化邪悟了的人到各监区害人,每天早上学习。管教把我和其他人错开学,不准我和其他人接触,怕我影响他们,我是坚决不听不信,动不了我。他们办洗脑班两个月,在七监区集中学习,我坚决不转化,并给他们讲:他们邪悟了,走错了,希望他们正悟过来,紧跟师父,这是旧势力迫害大法,我们应该坚定维护大法。他们要我写认识,开始我想给他们讲真相,写了几次他们不相信,我就不写了;他们让我做哑语体操,我不做我只炼法轮功,许管教就叫我站着。
在监区、车间,我利用机会讲真相,背《洪吟》,背经文,背《转法轮》给他们听。我说,电视是诽谤,我用事实道理来说服他们,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很多人都通过我们讲真相明白了,有的要《洪吟》看,有的要经文,有的要我给她们背书,有的说:我们回家后也学。
关在劳改队是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我应该出去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准备有机会就走。有一天王干事和一个监护从监区带我到车间,我看大门半开着,这是机会来了,我赶快走,我就往大门走去。还没到大门,我发现狱都管法轮功的余主任带几个参观的,我就在车间炼功、抱轮,被监护拉出车间,被余主任和男警狠狠的骂了一顿,并记大过一次,说我不劳动炼功超越警界线。二次我又往外走,在车间前大门正在上下货,我又往外走,当时是许管教值班,我说我不是罪犯,我应该出去,又没走成。
我每天坚持背法学习,不配合她们,下车间劳动,每天早上一到车间我就坐下来背《转法轮》一讲、《洪吟》、经文,回忆每一课内容,我能回忆多少就回忆多少,两天回忆一本,因为我不能忘了师父讲的法;同时还要发正念,每天就这样坚持着。
我开始背法时,干部经常来干扰,特别是许管教、罗队长,看见我背法、炼功就铐我,铐我也好,罚站也好,我都静静地背,把我吊在大铁门上,我都背,我每天必须要把法背了,我始终这样坚持着。我的包夹也帮我,叫我赶快背,不叫我做事,他对我也好,他也给干部说过,他不想包夹我,因为我也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
在车间有包夹,有互监组,在监室又有包夹互监组,只要一违规就扣全监室的分,任务重工作苦,点分不容易,又影响到减刑,所以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背法我经常被铐、被罚,小间那是经常关我的地方,我记得关了我八次,至少都是六天。就是这样折磨迫害,我仍坚持要学法。
在监室我讲真相,我自己做好,监室共12个人,在监室炼功,他们不干扰我,他们相信大法。我洪扬大法,把手抄经文给别人看,结果有次被二监室室长王雪艳给干部打了报告,把我借的经文也收了,还带了几个人把我床铺也抄了,又搜走了一本经文。我当时不在监室。
我始终坚持这样做,在车间背法,他们也就不管了,说我是老顽固。由于我不转化,他们不准家属接见,不准打电话,不准我和功友接触说话,发现了就要扣包夹的分。我想我和功友应该在一起,转化了的我都给他们讲,他们悟错了,我们应该坚持学法炼功,讲真相。高丽被转化后,外面就给她带进来很多佛教书和其它书,他们天天就看那些,也不学法轮功,把书在监区到处借,也给其他人讲,不学法轮功,学佛教,起到了破坏作用。我听到后就给那些人讲,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关键时刻看人心,我就给他们讲一些道理,把师父讲的修炼要专一,佛家功与佛教的区别讲给她们,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人,最后她们也明白了。
在2006年2月13日,我终于又回家了。今后我会更加勇猛精进,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