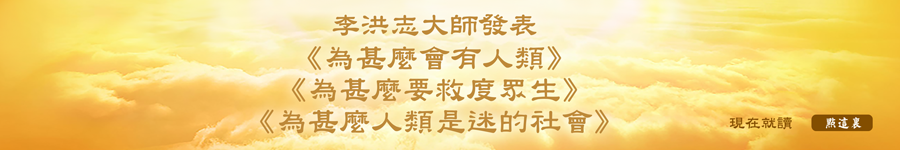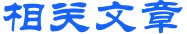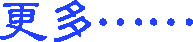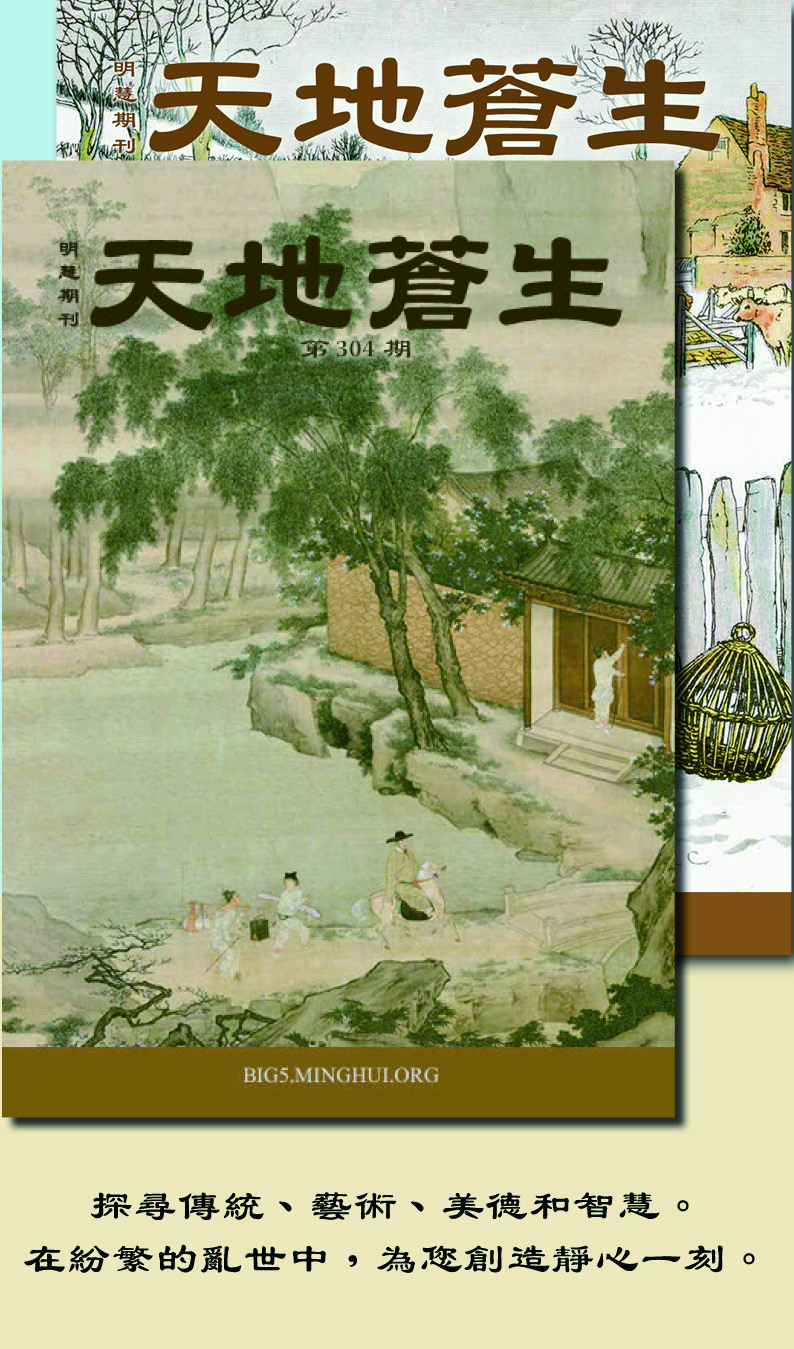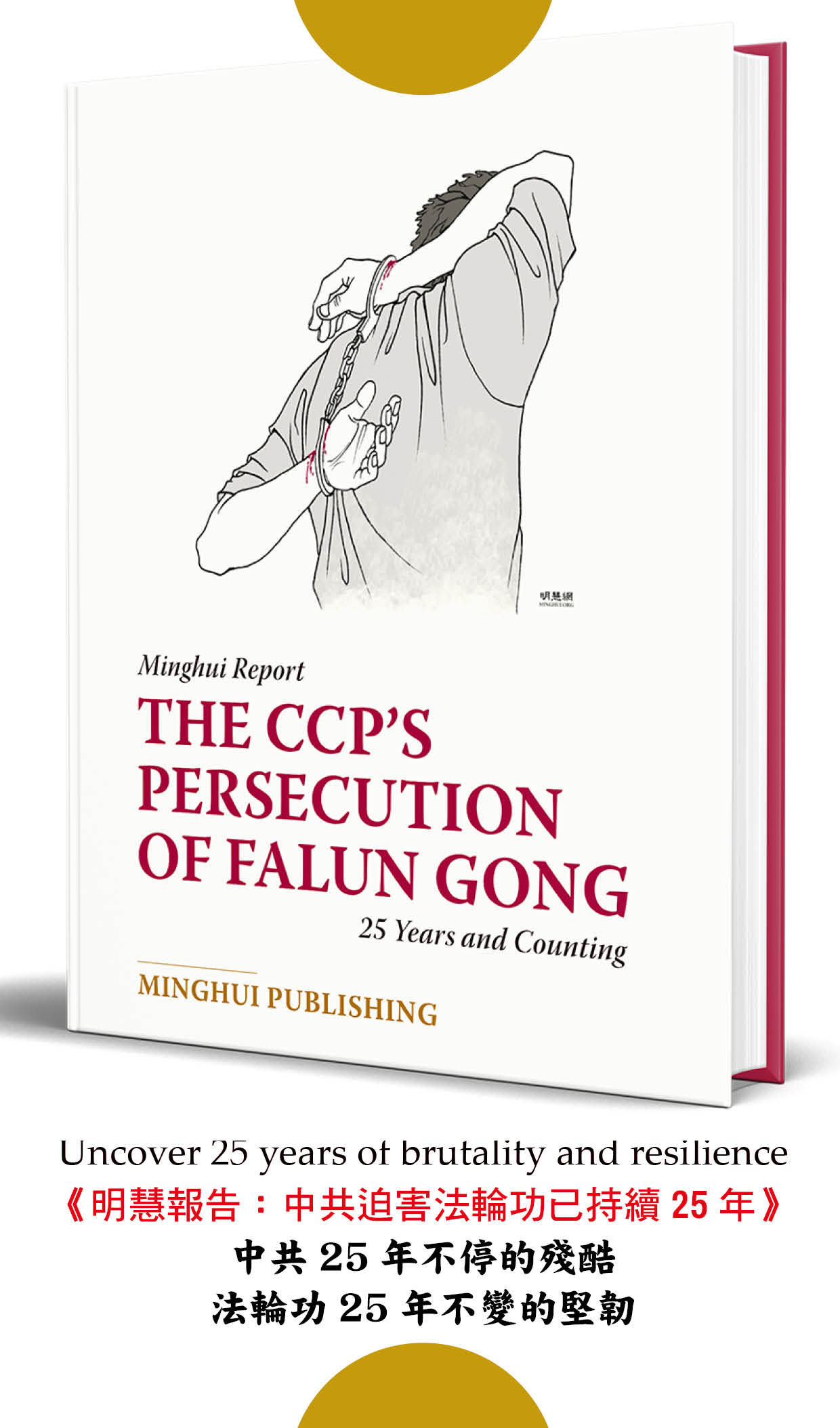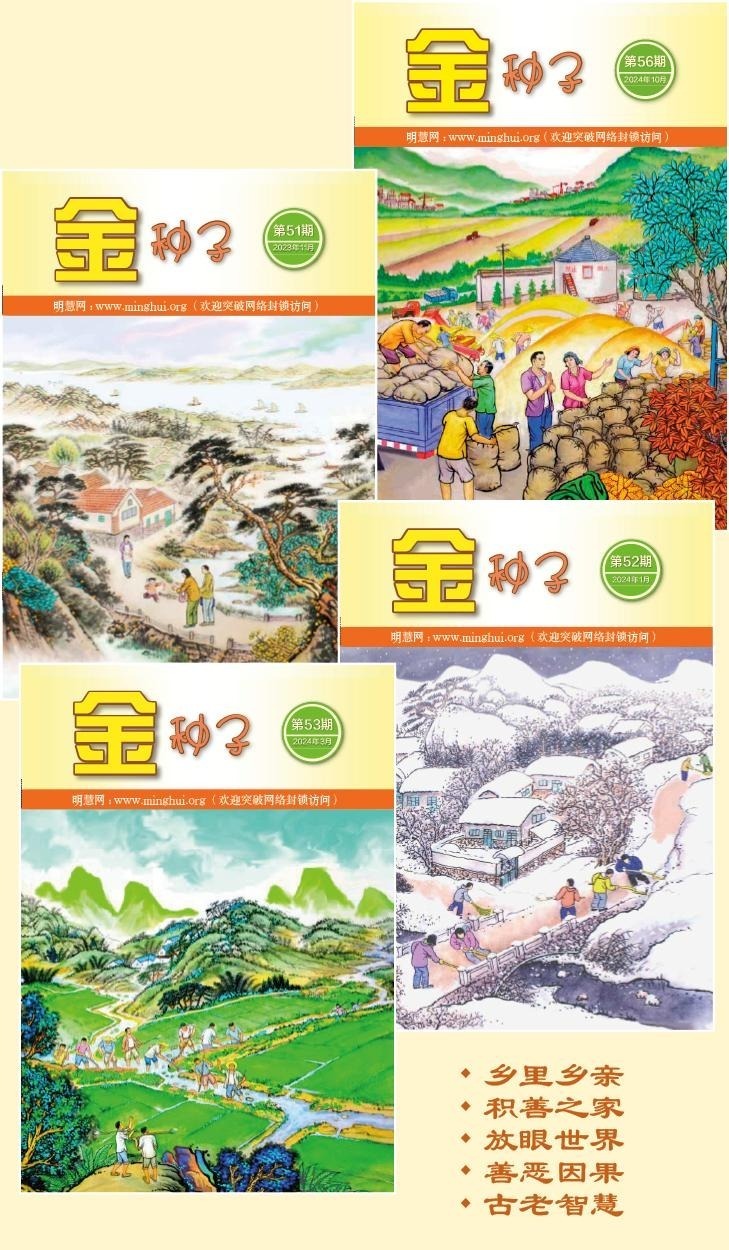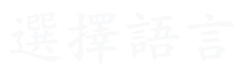遭十年冤狱、多次被迫害命危 曲德洪控告江泽民
下面是曲德洪在对江泽民的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叫曲德洪,原住鸡东县永安镇永新村。我以前脾气暴躁,修炼法轮功后,我一改往日的恶习,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努力约束自己不正当行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成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六一零办公室”,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正是在它的策划、指挥下,导致我遭受到了如下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动了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造谣、污蔑。我和本镇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为了向国家、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反映实际情况,证实法轮大法好,几经周折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北京各级职能、信访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所谓的民主、人权、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在北京,我们绕过了重重封锁,来到了天安门,此时的广场,军警特务遍地,到处是便衣,当我与外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刚坐在一块时,一个矮个便衣,拿着一个对讲机,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是法轮功吧?你们是来上访的吧?我知道地儿,你们跟我走吧,我领你们去。就这样我们一行近二十余人被他领到了 “天安门派出所”,结果被非法关在一个空屋内,有警察和“保安”不让说话,不让走动,他们满口脏话,并谩骂法轮功学员,我们都被禁止去厕所,我们的身份证被强行扣留。当时被劫持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共有四十多人。我们逃离了派出所,重返天安门广场。
九九年八月份的一天,我与全国各地的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南岛渔村吃饭,被北京国安、总参某部特务盯梢,在回住所的路上被一黑一白的两辆车子跟踪,上有两个红色的“警备”字样的车牌,大家发现后分头找机会摆脱他们。我和一同修被此二车紧紧跟踪,从黑天一直跟到半夜,满京城转圈,后被逼迫误入北京火车站,特务们伙同站内乘警绑架了我们俩,强行抢走我的手机,我不肯告诉真实地址时,他们去微机室查询,此时,我又被恶警们强行搜身,后又遭到谩骂,恐吓。我俩先后逃离了那里。
被国家安全局警察刑讯逼供
当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断的升级,各地的派出所、保卫科、政法委等邪党机关都陆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各处抓捕法轮功学员。我和其他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想让全世界的有缘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欺世谎言,我们召开了“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与会期间,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向来自外国各大媒体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因为上访所遭受的惨烈迫害。他们听到后感到很震惊,向世界各地做了及时的报导。
十月二十七日,江泽民在新闻联播里诽谤法轮功,第二天我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给了他当头一棒。
由于国安部非法监控了我们的手机,传呼机等,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九点多钟,在我们准备筹备“听证会”的过程中,我与另二位同修和《澳洲时报》的记者,在北京国际邮局门口相会时,被国家安全局特务一行二十人绑架。特务们带的胸卡为公安局,后得知胸卡是临时借来的,在车上警察们搜遍我们的全身,抢走了手机和随身带的所有钱物,蒙住双眼劫持至安全局专用的看守所。
送到审讯室后,由三个人合伙迫害,中间的只管问,两边的人各自记录。他们互相叫代号,都不认识。各有一个密码箱,“口供”放到密码箱中后两人交换箱子,由中间的人设定两箱的密码。当问我的姓名时,我不配合,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椅子上有一个铐子,铐住我的手,墙是泡沫的,是防撞的。地是软软的,水杯子都是塑料的。
 酷刑演示:铁椅子 |
他们说:“想死你都死不了,国际间谍到这都得服,不行整死你。整死你也没有人会知道,放明白点,江主席在法国下令了,把你们与会的顽固分子统统处死。就看你现在怎么做。”说话的特务是东北口音,四十多岁。另一岁数大一点的说:“不用问他叫什么名了,收拾他就成了,装什么孙子,靠墙撅着去,给我‘飞着’,两手抬高点(飞着就是面向墙,撅着低头哈腰,背部,后脑勺贴墙上,两个胳膊硬抬过去翻转后贴在墙上,手心贴墙)。”此动作由三个特务共同参与迫害的,其痛苦程度无法想象。折磨手段不断的变换,直到天亮,他们也没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他们从新发来的照片上认出了我,此时已是十一月一日了,有一个说:“才知道姓名,抓的日期就按今天算。明天给他送走,送北京七处去,基本上别想出来了。”
第二天,我被劫持上车,被蒙住眼睛秘密送往北京七处,一到七处,环境非常恶劣,厕所和床铺挨着,限制大小便,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小窝头,一点点菜汤基本没有油,几平方米的小牢房关了20多人,时值冬天我被迫睡在冰冷的地上。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睡觉,不停的恐吓。上楼时不让你走,而是两恶警架着我的胳膊(架着,脚基本不太接触地)。拖到预审室往地上一扔,又抬起来往铁椅子上一推,把夹板一放,狠狠的将锁头锁上,然后往那一坐,“啪”拍桌子一下,声音很大的说:“精神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北京七处啊,这没几个能活着出去的,都是大案要案。你现在就是我手中的一鸟,我让你松快点你就好过点儿。问什么说什么,不然收拾你。”
我什么都不说。一次从别的预审室过来一个“帮忙”的恶警,恶狠狠的对我拳打脚踢,用军用大皮鞋在我的全身乱踢。重拳加耳光在我的头上、脸上连抓带打,满脸是血,满身多处青紫,头发被一绺一绺拽下来,揪断的短头发混杂着鲜血,被施暴中喷溅到椅子周围的墙上,我曾几次昏死过去。
当非法提审我妻子张永丽时,他们对墙上的血迹解释说:那没事,那是腐乳汤,墙上有很明显的处理过的痕迹,但没擦净。我曾被多次提审迫害,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真是菜汤里几乎没有一点油,菜汤的碗底下面一层黑泥,菜叶上粘着小虫子。我们被饿的骨瘦如柴,那种感受真是度日如年。
大约十二月末的一天晚上,所有七处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全都提出来了,在走廊里排队,被分到各个北京所辖区的看守所,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分到通州区桥庄看守所,那里的看守人员也很邪恶,我多次被体罚,有一个外地的女法轮功学员被恶警把电棍塞进嘴中电击。妻子张永丽被四、五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六,在通州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了六名法轮功学员。(期间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亲自下令、直接指挥了对我们的这次抓捕、判刑,抓捕我们之前曾叫嚣:“抓到后统统处死。”只是后来被众多海内外媒体曝光,他们顾及到国际影响无奈作罢。)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劫持至天河监狱“南大楼转运站”。在那里不许我与他人说话,不许走动;妻子张永丽被北京通州法院诬判一年,被留在通州看守所遭受迫害。
正值北京的四月份气温升高,不给换单衣,很多在押人员只能偷偷的一点一点的往出拽棉衣裤的棉花,上厕所时再偷偷扔在便器里,如果被发现就会一顿毒打或电击。要定时去厕所,不到点不许去,有的人来不及就便到裤子里。历尽这里的苦难后,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我又被劫持到哈尔滨监狱。(当时江泽民下令所有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分回本省、省会监狱关押,也就是大刑期监狱。)
在哈尔滨监狱遭受的折磨
同年四月十九日被送到哈尔滨监狱(哈三监),到那先分到集训队,杂工组长杨金刚说:“你是全省第一个法轮功入监的,早听说了,等你一个多月了,必须转化了你。”那里的警察下令每天不许与别人说话和接触,用四个刑事犯包夹,晚上有一个犯人专门坐在我身边贴身看管,上厕所都得跟着。值夜班的犯人白天睡觉,其余三个犯人形影不离我左右,每天记笔录向警察汇报情况,家里寄来的咸菜、香肠、鸭蛋等被无理的告知:不转化的拒收,往返邮递多次,最后返回家中的邮包里的东西都烂掉了,而我却饿的骨瘦如柴(因哈监每顿只吃一小块玉米面板儿糕,用未成熟的面瓜蛋子当菜吃,而且没有一点油。玉米面都是一箩到底的,就是玉米直接加工,玉米骨头玉米须子都在里面。)恶警龚大伟还指使杂工组长杨金刚对我体罚,罚站,骑窄凳子,不许买吃的等。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我被分到二大队,中队长张雪滨(音)积极参与迫害,采用单独封闭,不许接触别人,用两个“包夹”迫害。有一次,因为我在监舍与几个犯人说话,被恶人告密,我被张雪滨叫到办公室说:你以后能不能把口闭上,不许再说大法好,什么话都不能说,就是当哑巴,能不能做到。我说:大法就是好,我说的是真话。再说平时生活我有说话的权利。张气急败坏,对我拳打脚踢,一脚踢在我的小便位置,当时蹲那就动不了了,差点痛昏过去,痛苦极了。刚缓过来站那,旁边一个恶警上去又打了两个大耳光子,说:整死你活该。这恶警可能姓刘,是个小队长。
二零零一年冬天,恶警战阴庆(哈尔滨监狱二大队干事)因我拒写“三课作业”,把我押了禁闭,并让包夹陪押,大冬天我衣服被扒的只剩一个裤头,和一套空心棉衣裤,一天两半勺玉米面糊粥,历经一个多月的冻饿打骂才解除禁闭。出来时体重仅剩八九十斤。
二零零二的冬天,我转交给法轮功学员卜繁伟经文时,被犯人告密,我被副狱长杨江云下令关押小号,小号内不让穿内衣裤,只让穿空心棉衣裤。张雪滨和大队长对我非法提问:“谁给你的经文,说出来就放你。”我不说,恶人就加重迫害。禁闭的地方有一个恶警,他唆使犯人打我,并告诉说:“别说我说的。”每次犯人打半天了,他才过去假惺惺的说:别打人,不许打人啊。回过头再与犯人递眼色。
十多天后我生命垂危,他们才找来狱医,我人已经脱相了,前胸贴后背奄奄一息,一看不行了,才抬到医院,所用的药物强行让我家人支付。住了十六天才勉强脱离危险。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被释放的前一天,六一零头目陈树海,由于我不配合其用专车送回家,陈树海又气急败坏的把我押入小号,并出动四恶警手拿手铐、电棍、铁链等凶器威逼我写三书,说:“不写别想离开哈监。”最后把我拘禁在小号里锁上脚镣,戴上手铐。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他们用小轿车,四个恶警(包括陈树海)给我戴着手铐,穿着囚服,(家里送的便服没给换上,他们知法犯法给一个出监的合法公民穿囚服、戴手铐。)夹在他们四人中间,经八、九个小时才送到当地,交与当地610、政法委、派出所,我下车时腿都不会走了,中途上厕所都不给打开手铐。
在哈监被迫害的三年多,体检都是只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我多次被强行化验血型、体检,他们把我的身体资料记录在册,也许就是为摘器官时备用。
鸡东国保大队对我的摧残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家乡的永安派出所和鸡东国保大队一伙近二十人再次绑架我与妻子,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永安派出所黄姓指导员、李姓警察到家后先把我一家人稳住,然后唤来了在外面等候的鸡东国保大队不法人员。三辆车,十多个人,他们蜂拥而来,领头的国保队长叫于洪军,副队叫孙作恩。他们进门就到处乱翻,屋中一片狼藉,在没有翻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把我和妻子带走。
在鸡东公安局五楼,其中一个副局长幕后指挥于洪军对我施用各种酷刑。他说:抓你来知道为什么吧?说吧,还有……不说整死你,整死你象杀个小鸡似的,告诉你,我不缺钱,给钱也不好使,我只要“政绩”。我就不信整不了你们,给我往死整,把他铐架子上。他们先把我的鞋袜脱掉用白龙管打,两个恶警换班打,你一下,他一下的雨点般的往下打,这两个恶人叫何文清和崔光日。边打边骂,不一会脚胀得青紫很粗,很大,钻心的疼痛,几次昏死过去。然后,于洪军再用锥子扎,副队长孙作恩也积极参与。
这时,崔光日上来把着我,还有何文明和几个不知名的恶警一拥而上,何文清用灌注了水泥的实心白龙管,用力狠狠的打我的双脚,听到打在骨头上的声音,水泥块洒落了一地,一恶警说:这也不结实啊!崔光日说:“里边起连接作用的油门拉筋也脱落出来了”。于洪军说:“把拉筋给我,这玩意打人更疼”。便往脚上狂抽,再用锥子扎,几次反复打扎,其痛苦完全超出人的想象。
我又几次昏死过去,他们就再用凉水往我身上和脸上浇,激醒我,我始终不说话,天快亮了,何文清气急败坏的抽出了我裤子上的大宽牛皮带,扒开了后背,沾着盆里的凉水往死里打,休克过去就用浇花的喷壶往脸上身上喷醒,再打,再喷,于洪军、孙作恩又把我的头发拴上吊在架子上,说叫:“头悬梁锥刺股。”用火柴棍把眼皮支上,怕支不住就再用胶带粘上。用锥子到处扎,一看还是不行,一会过来一个副局长,领来一个狱医来了,说:检查一下,死不了就行,于又说:“没事,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大夫掌握,就是让你遭罪。真死了也就是杀个小鸡一样。”他们用尽了损招,我已被他们折磨的奄奄一息。于说:“要不让你俩口子在一起审,弄你让她看?”
被鸡东警察灌不明药物、芥末油
这些打手又生一邪招,用浇花的喷壶往耳朵里注水,这耳注满了,再往那耳里灌。(原来水里有破坏神经的药物),于说给他喝点水算了,这时拿来一瓶矿泉水硬给我灌下去了。过一会,于把我拖到他跟前用脚踩我的头和肩头,拿起扫地的扫帚往我的嘴里捅。于用脚踩着我的头说:真好玩儿,这东西真好使。(指药物)
这时我已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他们用力一拍桌子,我就吓的一抖搂。药劲一上来了,他们就开始用别人的“口供”诱骗。期间,东海矿的顾爱民,八五一零农场的李崇峻等几名法轮功学员也都被灌了药物。
十一月份的一天傍晚,于他们把我提到预审室,并告诉室内看守说:“今晚不一定送回来了。”他们带着水果,饼干,矿泉水等诱骗,一看不好使,崔光日拿着厚书垫在我的胸部等位置,用力猛击,让撅着,飞着,用手把着持续体罚,并用烟头烫手等部位。折腾累了,他们说给他喝点水吧,何打开一瓶给我喝,我不知是药,崔说行了,行了,又喝多了。还有一次,于和孙等又来了,每次从鸡西“提”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来找我实施迫害。孙说:“那天去八五一零发传单时,中途下来的那人是谁,就你认识,快说。”于又说:“不行带局里去,单独整,收拾你一夜”。孙用牛皮的皮带拴起来打我的手心,最后把皮带也打折了,他也累了。要往我的鞋里灌水。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我与其他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十一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他们就用鼻管插管灌食,往奶粉里加大量的咸盐,给我锁在七号监舍的地环上,每次灌食时才打开抬出去,往出抬时,过门槛时,特意往下蹲,往角铁上磕,腰骨时常被磕紫,碰伤。最后要求家里拿一万元钱就放人,由于家里没给钱又把我在七月五日送至鸡西司法局医院迫害,此医院杂工犯人积极参与迫害,用钢勺硬扒嘴往里塞,弄得鼻孔出血,用瓶子猛击脸部,眼部被弄成黑色伤痕,又把被褥用水浇湿,我奄奄一息的躺在冰水被褥上,他们没办法又把我准备弄回看守所,因鸡东法院的两千元钱已用完,不交钱就得出院。
去接的副所长王延国恼羞成怒,对从所里带来的两个劳动号犯人说:“不用抬,扔地上拖着走就行,车离这还挺远呢。”我线衣被地上的沙石磨烂,血肉模糊,造成衣物粘在肉皮上。王延国又说:“一会见到食杂店给我买点治吃饭的药,据说这药很灵,就是芥末油,买辣根那种。”然后停车买了两瓶芥末油,回到看守所后,把我直接弄到预审室进行迫害,王延国说:“把他放地上就行,开始吧”。姓杨的两个犯人用力按住我说:“看你吃不吃?”打开芥末油瓶盖,顺鼻子往里灌,此时我被弄的仰面朝上躺着。
一灌下去就窒息昏死过去,醒过来再灌,连续数次。并往小便的尿道口里抹。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还是摇头拒食。过后那个姓杨的劳动号说:“当时被折腾得真挺可怜的,一灌下去,就象小泥鳅,直翻个,直打滚。没办法,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也得往里灌哪”。王延国又说:“行了,再弄就整死了,死了没啥玩的了。先给他抬五号监舍去,上倪鹏(牢头狱霸)那个号,不行就整他,那小子不会惯着他。”
在五号又灌了三天后,倪鹏与王延国突然密谋,说:“明天上面要放他,今天就得下手了。”他们准备了绳子(把被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把我倒背手五花大绑,把嘴勒上(怕咬舌头),推进水龙头下面,(厕所蹲位)扒光了的我被两个死刑犯人(于永生、王铁)把脚链子缠在我的脖子上在上面踩着,另一个犯人叫王铁的用大盆接水龙头里放的凉水往我的头上一盆接一盆的浇,我多次被水窒息,昏死。倪鹏在监室内指使这些人迫害我,王延国在窗外走廊里走来走去的当总指挥。直至我再次生命垂危,他们才停止迫害。
在佳木斯监狱的煎熬
后来被鸡东法院非法判我六年冤狱。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我与当地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鸡东看守所劫持至牡丹江集训队,经二个多月的非法关押、迫害,强制奴役,六月份,我们被牡丹江监狱用专车、出动七名持有微冲、短枪、械具的警察,劫持至佳木斯监狱一监区二中队,我对二中队长王德祥说:“我不是犯人,我也没有罪,我也不能为邪党创收,让它继续迫害广大民众,迫害信仰。”我坚持不出工,教育中队长张士军和指导员刘焕,找我到办公室做笔录:你不出工就押你禁闭,你不出工了,这个口子一开,都不出了。(王德祥找犯人王越等人打我,被犯人们拒绝,后又想到关禁闭迫害我)。大队副教魏建敏也威胁我,过完年再出也行,要不就押你。我说:押,你也押不成,你说了不算。我不在笔录上签字。
“教育干事”张世军和刘焕用手铐强行把我连拉带推抓胳膊摁肩头就给劫持至禁闭室里去了,小号看守扒去了我的衣服,只剩裤头,然后仅给一套空心棉衣裤,多处没有棉花,多处有窟窿,没有扣子,没有腰带,没有袜子,鞋也没鞋带,里边全是湿的,天花板上能看到天。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暖气片被厚铁皮盖着,仅有一些个小眼散发出一点温度。
因我绝食抗议,三天后监区、狱医、狱护等人员野蛮灌食,他们在奶粉中放入大量咸盐,用铁器撬我的嘴,我的牙齿被撬裂。嘴撬不开就从鼻子往里灌。到第八天我已第二次生命垂危,小号警察怕我死里头,就叫一监区来人用三轮车送我去了医院,到医院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左手四个吊瓶,右手三个吊瓶。医院说:下午送来住院吧!到医院又是强行灌食,由于长期迫害,我尿不出来尿了,被狱医野蛮插管导尿。用绳绑手强行打针,教改科副科长曹建武到医院安排强行给我打针,而且找来了我的姐姐,儿子等五、六人劝说我,费用花了二千来元,给我家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我的家人看到我被迫害成这样了,非常难过,幼小的儿子悲伤无奈的望着我。最后,他们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同意我不出工了。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在迫害初期,我一家四口人被迫害的天各一方,我被关在北京和哈尔滨监狱;;九岁的儿子被公安部王副部长软禁在招待所,七十多岁的老母独自在家无人照顾。
二零零三年,我刚从哈监回家五十天,永安镇派出恶警上门骚扰,逼迫我按手印,做材料,此时我的母亲正在病危中打点滴针,恶警的无理要求,大声喧闹,使我母亲十分害怕,扎着吊针的手在颤抖。由于这次受到了极大惊吓,病情加重,二十多天后,母亲张世清(法轮功学员)带着对儿孙的无限牵挂含冤离世。给我们全家众多的兄弟姐妹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这一切都是江泽民执意迫害造成的。
二零零四年秋天,由于我被鸡东国保绑架,他们扬言一定要对我判刑,孩子上学成绩非常好,总是全班第一,老师们都说是清华大学的苗子,可当我被绑架后,校长、老师都说:你爸爸是法轮功学员将要被判刑,子女考上名牌大学也不让去,造成我儿子一度心理负担,学习成绩急速下降,孩子在痛苦的煎熬中只考了一所自费的普通大学,给其心灵造成了永不愈合的创伤。所造成的精神损失、经济损失,无法用数字估量。
二零零五年十月末,在狱警室,法院人员强迫我在离婚协议送达书上签字,我一直深爱着我的妻子和我们那聪明可爱的儿子,我不想让这个家庭破碎,所以我拒签,看守所内的恶警裴某说:“不签也得签,欠揍,扒你的皮,我去取白龙管子,给你开管”。这时有一个叫姜军的狱警拉他一把说:“拉倒吧,拉倒吧,签完给送回去得了。”法院来的人拿着签完字的送达书,哈哈大笑着说:“这下可解放了”,显然妻子也已被他们所威胁。这些不法人员这一行径已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级指使永新村“没收了”我地里已经成熟的三十亩粮食,永安镇长徐贵勒索了我家两千元,派政法委人员去北京接关押在那的我的孩子,他们用这些钱在北京游玩。我二哥曲德方很有工作能力,竞选村长时,镇长徐贵扬言说;“你弟弟炼法轮功,选上也不行,我知道你能选上,那也白扯。”江泽民搞的株连九族的迫害断送了我哥哥的前程,造成了精神与经济的重大损失。
出狱后举步维艰,又被密山警察迫害奄奄一息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从佳木斯监狱迫害六年释放,面对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已无家可归,勉强打零工度日。但现实生活中一切通讯工具一直被安全局长期非法监控。一善良的刘英女士同情我,与我组成了家庭。三年后我和刘英又被鸡西安全局伙同密山公安局砸门撬锁、绑架抄家,无法无天到居然用风焊把我家的双层防盗门割开三十公分左右的大三角口子强行闯入。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晚间七点多,鸡西市公安局、国安局宋文爽伙同密山市政法委书记钱国锋,“610”主任于晓峰,密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王耀光,中队长玉海颖等人闯到我家,用风焊把防盗门割开一个大三角口子,非法闯入,企图抓捕我。当时我不在家,警察便非法抄家,抄走我家的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及现金等私人财物,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六点多钟,我在佳木斯客运站被佳木斯安全局伙同鸡西市国安局宋姓支队长、张洪涛、公安局国保警察关斌等几人非法抓捕到鸡西市安全局,抓捕时,他们三、四个人一齐压向我的头部,我的头被重重的砸在水泥地上,当时就抢掉鸡蛋那么大面积的一块皮,鼓起一个大包,至今未愈。
警察以找伪基站的下落为由对我实施迫害,给我戴手铐,在车里有一个警察头目冷不防照我的小腹爆发一拳。当时就上不来气了,好半天才缓过来。提审时警察关斌拿鞋底抽打我的脸。鸡西安全局审讯室的墙都是泡沫的,大铁椅子左右都有固定着手铐,固定的捆人的大皮带,我被关押三天后才送鸡西第二看守所。
在“审讯”我无果的当天晚上,他们利用非法监控电话的方法,在我岳母家门前蹲坑,强行绑架我妻子刘英,四个警察把我妻子强行推小轿车,四个男警察把我妻子挤在中间座位上,并口说脏话、污言秽语。并对刘英刑讯逼供,国保警察关斌、姜云鹏用高压电棍轮流电击刘英,江云鹏把电棍的两极接上铜丝,铜丝的另两极分别绑在刘英的两个大脚趾头上进行高压电击,高压电棍电遍了刘英的两条大腿、小腿、一直到脚,到处可见血迹斑斑出了很深的血坑,关斌把高压电棍插到刘英嘴里电击,直至把电量耗尽,共电击迫害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切过程,宋姓支队长一直在身边监督,且从绑架到酷刑过程中没有一个女警参加,无法无天的侮辱人格、侵犯人权。而且电击女性大腿等部位,构成了猥亵、酷刑、逼供等多项犯罪。刘英被迫害的腹痛、头晕支撑不住了,他们才将她放回。
我在鸡西市第二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因头部负伤、剥夺睡眠等迫害导致心律加快、胃肠不适、造成进食呕吐,浑身颤抖、不能进食,遭到关斌等警察的强行灌食。国保大队刘立臣始终伙同参与迫害。在我身体不能行走的情况下,强行让犯人背出“提审”,造成昏迷晕倒不醒,叫120送到矿总院抢救,所花的一千多元医疗费全部强迫我妻子承担。而且是晚上八点多三百多里路把我妻子骗去的。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才被家人“取保”(取保押金三万元。)回到家中。
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那些仍遭受惨绝人寰迫害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所有迫害手段,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没有亲身经历,永远都无法真正想象到江氏集团这灭绝人性的迫害是多么残酷。因此据十七年江泽民及其帮凶为了达到其妄图根除法轮功的目的,对作为信仰群体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他们已经触犯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犯有群体灭绝罪、危害人类罪、酷刑罪等国际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