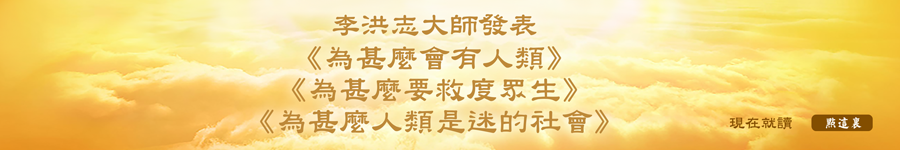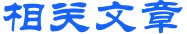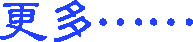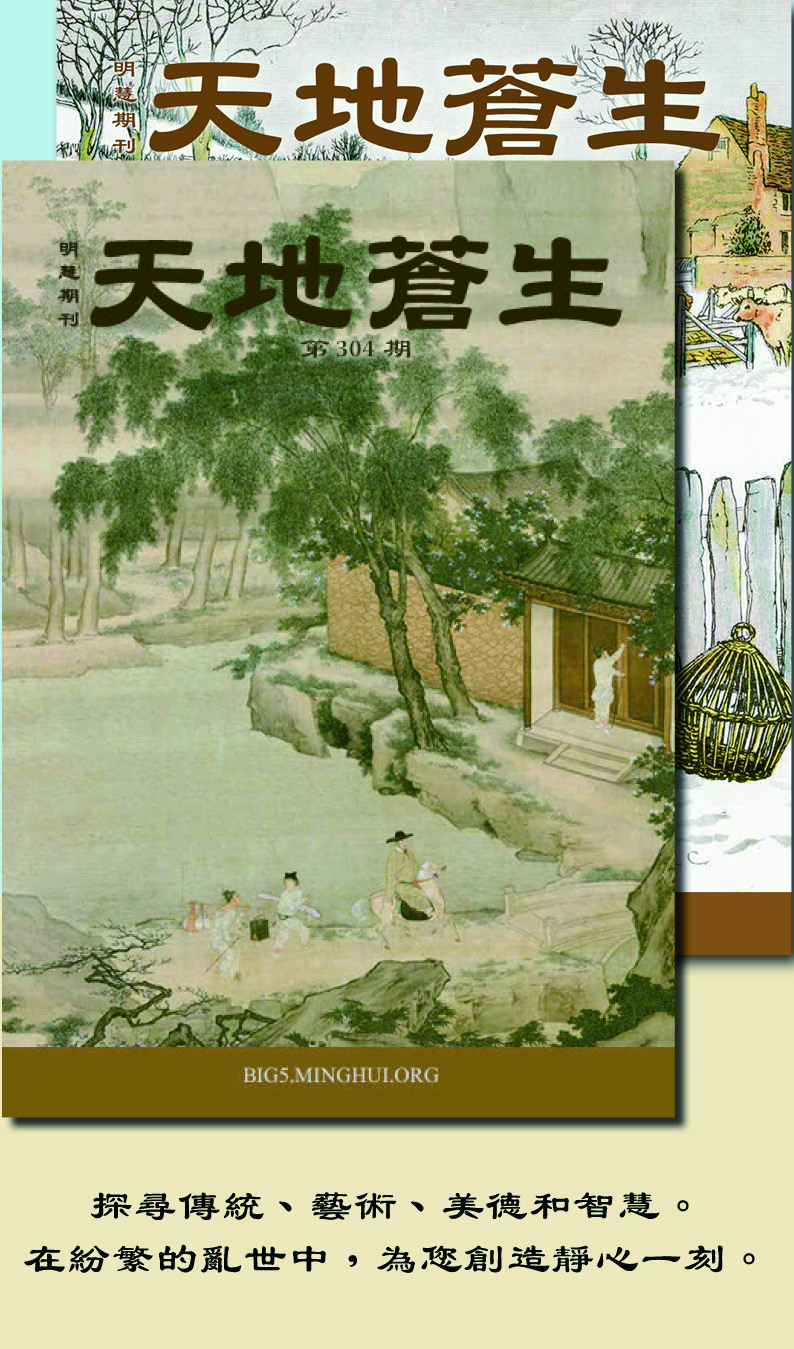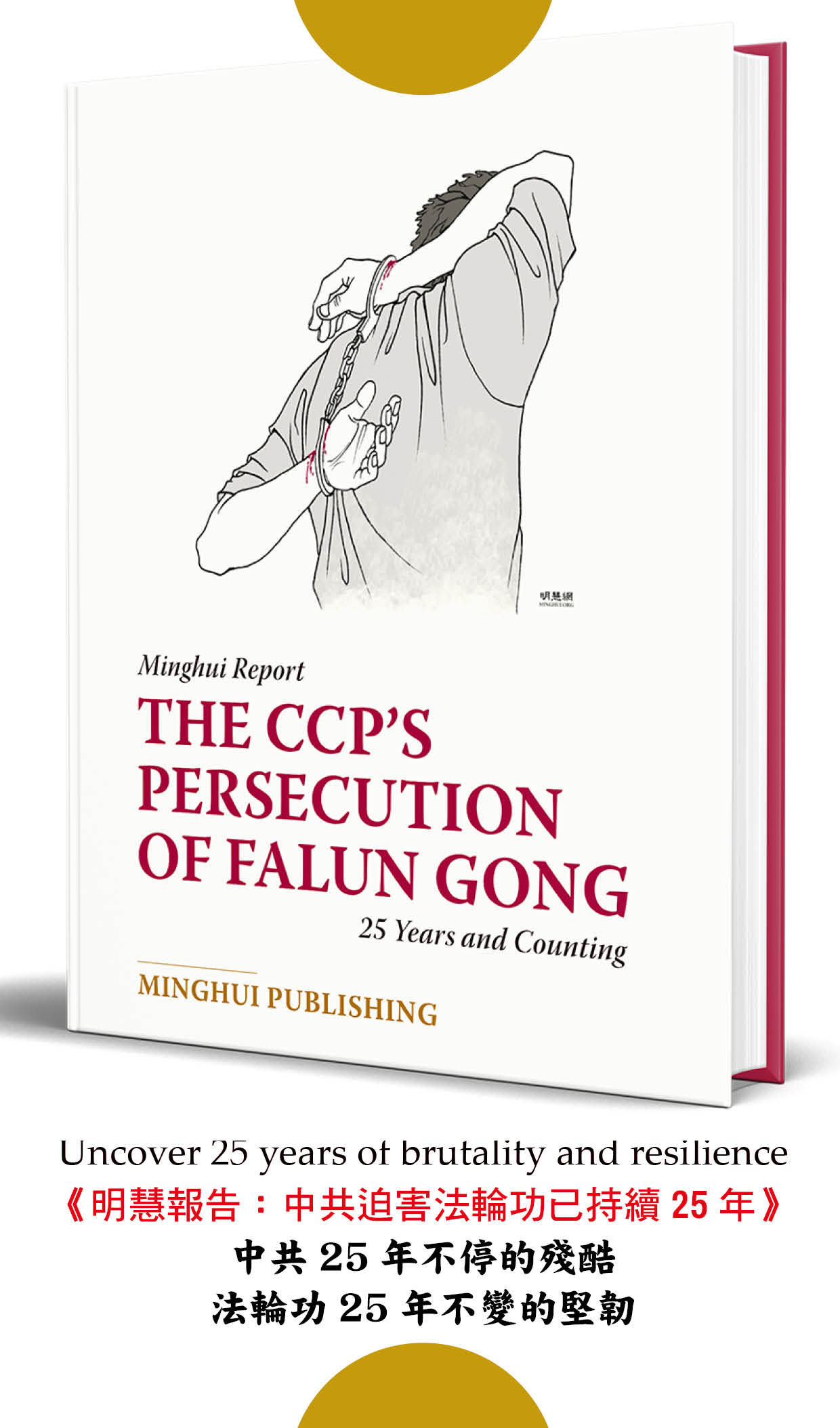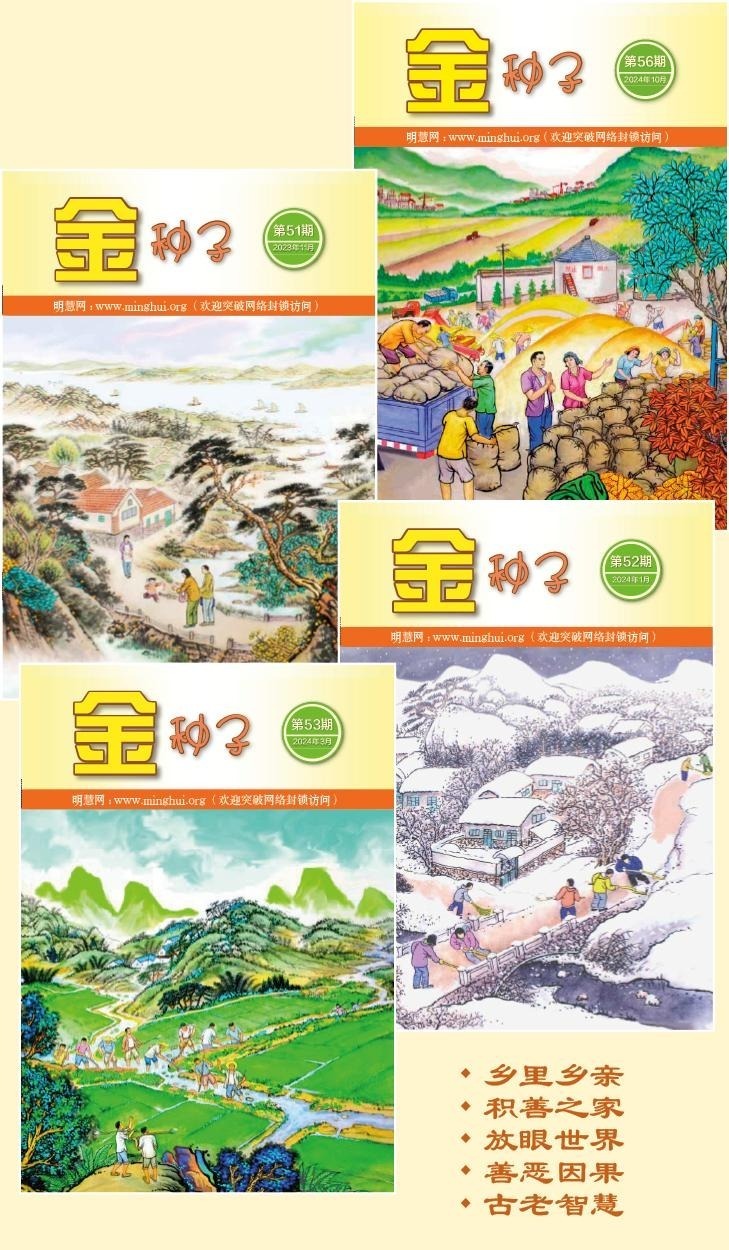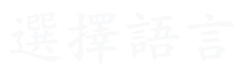黑龙江双城市白艳被警察殴打折磨的遭遇
一、修法轮大法 明白人生意义
我叫白艳,出生于一九七七年,家住在双城市新兴乡新洪村。一九九八年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刚看了一段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心里就平静的象一面镜子。虽然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可心里总觉着人活着真苦。慢慢的通过看书、学法,我才明白人为什么活的这么苦,人来到世上的真正意义。只有按照大法的法理“真、善、忍”去做,遇事多替别人着想,没有执着,才活的轻松、愉快。在九九年我走入当地学法点,通过学法、修炼我心里踏实、愉快,明白了我此生的意义。
二、遭村委会监视骚扰 几年流离失所 回家后遭绑架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村委会派人监视炼法轮功的人,每天到家查看在做什么,连出门都要向村委会请假,特别是他们所认为的“敏感日”,有时来家二至三次,怕我去北京上访,我和家人都受到了干扰。
为了家人不受他们的骚扰,我离开了家,去了哈市打工(给人家做保姆),过了一段时间,村领导和派出所的人到我家问我去哪打工了,家人怕他们又来干扰我,便没有告诉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哥哥不想让我在外面吃苦,二零零一年冬天,哥哥把我接回家。我碰到村委会的人,他说:“派出所的人还在找你呢,你还不快走。”这样,我又离开了家。
二零零二年正月初五,我回家过年,第二天正月初六村支书(王国书)打电话告诉派出所说我回来了,有人告诉我的家人说,一会儿派出所的人要来抓我。我当时想我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躲着他们,就去了同学家。过了一会儿,家人来说派出所的人到处找你呢,你赶快走吧。
我刚走,就被他们截住了,村治保关英龙领着几个人没有着装,就说是派出所的,便强行将我抬上车,只因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被他们推打到车的前排座和中排座的中间塞到那里,(他们说:多亏走的快,一会儿家人来了,走不了。)
三、在派出所遭恶警殴打 非法拘留十五天
他们把我劫持到派出所,给我戴上手铐,开始做笔录,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按“真、善、忍”去做。他们说那就是还炼,给我写上炼。我当时想,他们要以这种借口迫害我,便上前撕碎他们的笔录,他们恼羞成怒,派出所的白玉桥拿了一个棍子用力的向我的腿打来,范业满用力向我的头顶砸来。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白玉桥拽着我戴的手铐往二楼上拖我,手铐勒到了肉里,卡出了血,便改拽头发。
拽到楼上,他们让我跪下,我说父母我还没跪过呢,我是不会跪的。他们把我推倒在地,用脚踩着我的头,脱去我的鞋,范业满和另一个人用塑料管(又称小白龙)打我的两个脚心。我当时没有怨恨,就对他们说,大过年的你们不要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范业满和那人打了一会儿,打累了便停了手,白玉桥却邪恶的说:“你看我不生气,我笑着打你,我打……(指师父)呢。”我听后很难过,这时才想起他们这么打我,都没有疼,心想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刑具:恶警抽打法轮功学员的白色塑料管,也称作“小白龙”。 |
他们看我没怕,便用伪善来骗我,范业满说;“来到这坐下,这回你怎么说,就怎么写。”做完笔录让我签了名。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说:“回村上核实一下,就放你回家。”他们把我骗上车,但没有回家,却向着双城方向开去,途中他们对我说:“你身上有多少钱,给我们转交给你的家人,到了看守所都得没收。”我没给他们。途中又上来一个人,他们说:“这是我们所长,你不相信我们,你把钱给我们所长。”我说我兜里的钱是干活那家多给开的工资,我干了二十天,老板看我干的好,就提前给我开了一个月的工资,我回去时得还人家。
他们把我拉到了双城市公安局,就凭着按“真、善、忍”做人,先进去,批了一个十五天拘留,然后把我拉到了双城市拘留所,让我在上面签字,我不签。他们要打我,所长没让。说你签不签都得拘留。我在上面签了字,拘留所的一个人让我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说是出来后给我,我把二、三百块钱和一个传呼机拿了出来,他们中有一人说:“就这点破钱。”拘留所的人说;“呼机不能保管。”他们说:“我们给拿回去,给你家谁?”我说给谁都行。(我回家后问起呼机时,家人说没有给)。
四、在第二看守所遭灌食迫害
我被关进第二看守所一监室,进去后有人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说炼法轮功,她们说赶快上来,原来这里关了很多炼法轮功的人。在那里我开始绝食、绝水来抗议他们对我的非法关押。到了第六天时,我洗头发、洗衣服,一个刑事犯说:“如果是别人说,我都不会相信,六天没吃没喝还能洗衣服,真神了!”
到了第九天时,他们强行给我灌食,两个刑事犯按住我的腿和手,狱医刘洪志拿着一个胶皮管子往我的鼻子里插。一开始插不进去,后来鼻子被插出了血,我说你们把我鼻子插坏了,看守所的狱医刘洪志说你还挺明白的。灌食后,他们给我转到了九监室,我的身体冷后开始热,逐渐的嘴干裂,内脏开始烧膛,那种滋味无法形容,只觉的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难熬。我瘦得脸的皮都紧贴在骨头上。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
第十三天时,他们把我叫出去,说让我喝点水,他们说给我往上反映。回监室后,我开始吃饭。当地派出所孔庆满和范业满来非法提审我,孔庆满给了我一个嘴巴子说: “你瞅你那样,抓你那天我没在,(意思是他要在,好好打打我)”。范业满说:“刚开始时可没这样”,(也许是才十几天,我就被迫害的前后判若两人)范业满说:“要不然,我给你买点吃的”,我说不用。
在我吃饭的十多天后,监室内有几个同修绝食反迫害,(在她们绝食的第三天,我开始第二次绝食),过了六、七天有一同修出现昏迷,看守所通知家属把她接回。绝食到十来天时,看守所的人把我们叫出去,狱医刘洪志给我量血压、听心脏,(先量一次,不知是没量着,还是太低,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很惊讶。)又量一次,说我不适合灌食。当时要给我们四人打针,可是一看药只有三瓶,他说:“你的精神状态都很好,这次就不给你打了”。
又过了两、三天,有几个同修出现了生命危险,看守所怕承担责任,便把几位同修送回家,可是过了五、六天,其中两个同修又被押了回来,这时才知道,把她们送回家,但没有放,而是有人看着,等她们在家吃了几天饭,身体刚有好转,就把她们抓走直接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因检查心脏不好,万家拒收,这才又被关进看守所。
当时我还在绝食,这次不象上次那么痛苦,不冷也不热,也没有烧膛的感觉,有时嘴里还冒出一股甜水。监室内一刑事犯阿姨问狱医刘洪志,“一个正常人不吃饭,能挺多少天”,刘洪志说:“正常人能挺七天。”阿姨又问:“这个小姑娘都十四、五天没吃没喝了,还能洗衣服,而且没有异常反应是怎么回事?”刘洪志看看我们,无言以对。
看守所的人把我叫出去,刘洪志他们强行给我打了点滴。不知里面放了什么药,回监室后,我的手慢慢的开始干裂、象土豆开花。记得是星期五,看守所的所长刘清禹到关押我们的监室,用手指着我说:“白艳如果你还不吃,我决不放过你。”
在头一星期前,他们说我不适合灌食,可是在我绝食的十七、八天,星期一的早上,把我叫出去,刘洪志他们却强行给我灌下去两盆高浓度的盐水。灌完后,两个刑事犯把我往监室抬,盐水通过我的鼻子和嘴往外冒,回到号里,有人说快喝点水,把盐水往外吐一吐,要不然胃会受不了。我喝了点水,又返出了许多盐水,吐得衣服和裤子上都是白花花的(同修把我的衣服洗后,衣服和裤子上还是白的,洗了几遍才洗掉)。
不一会儿,盐水往我的头上拱,使我的头剧痛,监室内的人看我疼得那样,都被吓哭了。这时,有一个同修说:“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种状态。”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想是呀,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种状态,随着我观念的转变,盐水下走排出,剧痛慢慢消失。当时我想他们这么迫害大法弟子,造下的罪业将来得怎么还呢?为了他们的生命着想,我决定不绝食了,放下执着出去的心,就这样我开始吃饭。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眼睛看不太清,特别是早上,洗完脸后能好些,(这种状态持续一年多)。右腿剧痛,都不敢碰,下地上厕所都需要同修搀扶,没用医治三天后,右腿一切正常。
一个多月后,有一个青岭乡的男大法弟子叫吴宝旺被迫害致死,所有监号的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抗议三天。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新兴乡派出所所长和姐夫来接我,所长让我在一个三千元的单子上签字,我不签,所长说:“你就快点签了,这钱以后给你。”我就在上面签了字,看守所让姐夫交了饭费,我才被接回。
五、家人被巨额勒索
我回来后,慢慢的才知道,因为家人怕我承受不了,一开始没有告诉我。家人说:“你刚被抓进去时,便找人打听你在里面的处境,派出所传话说交八千元钱第二天就放人。”只因我的母亲当时已七十来岁,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在我十四岁时去世,哥哥和姐姐们的家条件也不是太好,哥哥和姐姐们连贷带借凑了八千元钱给了他们,可是人却没有放。
我的家人天天在期盼着我能回来,精神在一天天中煎熬。就在绝望的三个月后,派出所让人捎信再拿三千元钱去接人,嫂子听后,就哭了,一是哥哥到外地打工没在家;二是家里实在没有钱,到哪去借?三是凑到钱给他们,人能不能回来呀?姐夫在邻居家贷了三千元钱,抱着一丝希望,把三千元钱给了他们,又多给他们五百元钱,让他们去吃饭。
对于那些迫害过我的人,希望我们大法弟子的纯正善念能唤醒你们那尘封已久的、内心深处的良知与善念。不要再助纣为虐,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了,挽回你们造成的损失,为自己、为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最后祝愿你们与你们的家人都能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