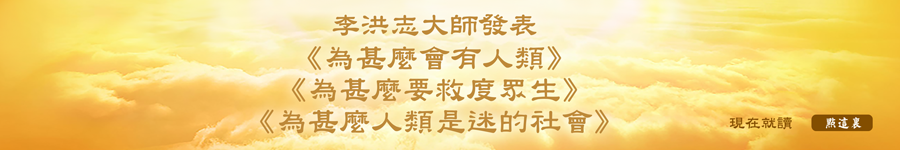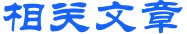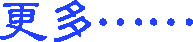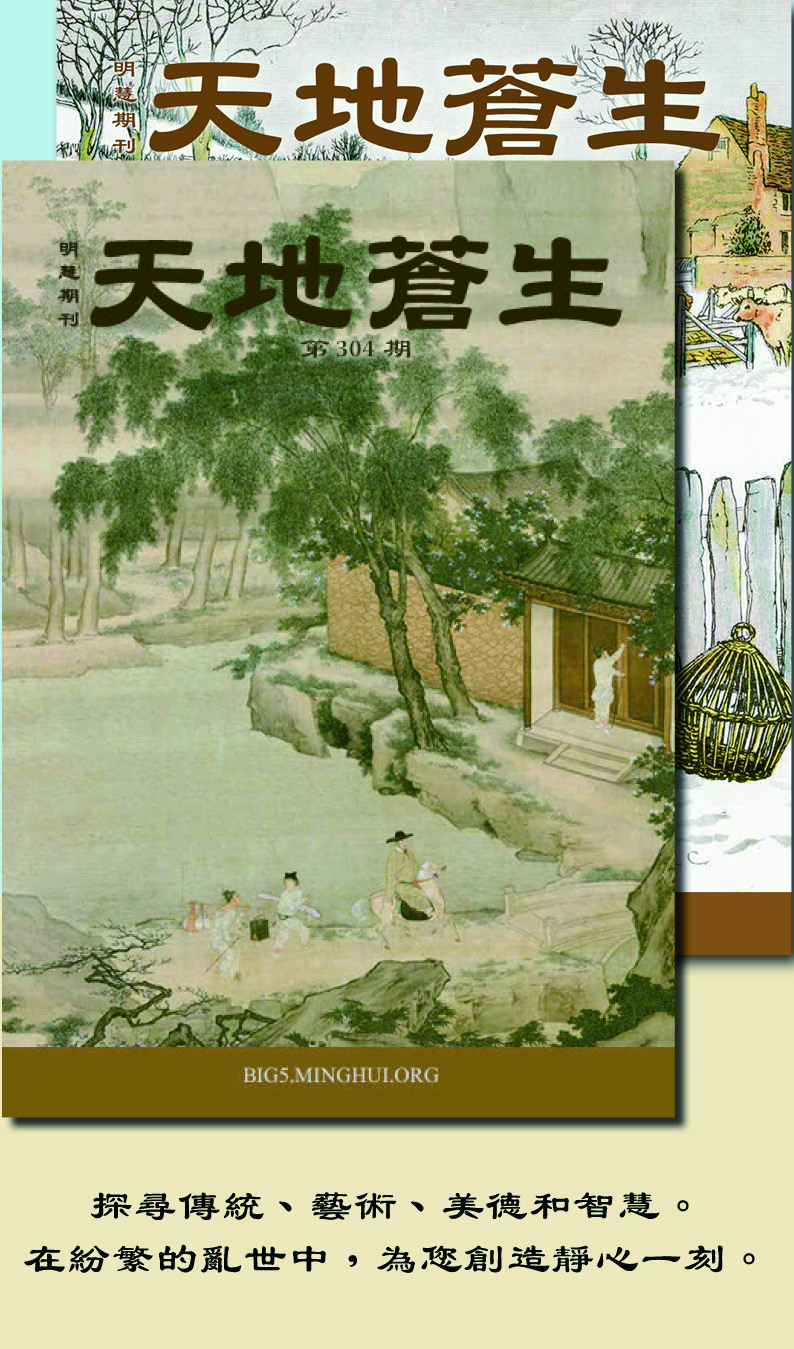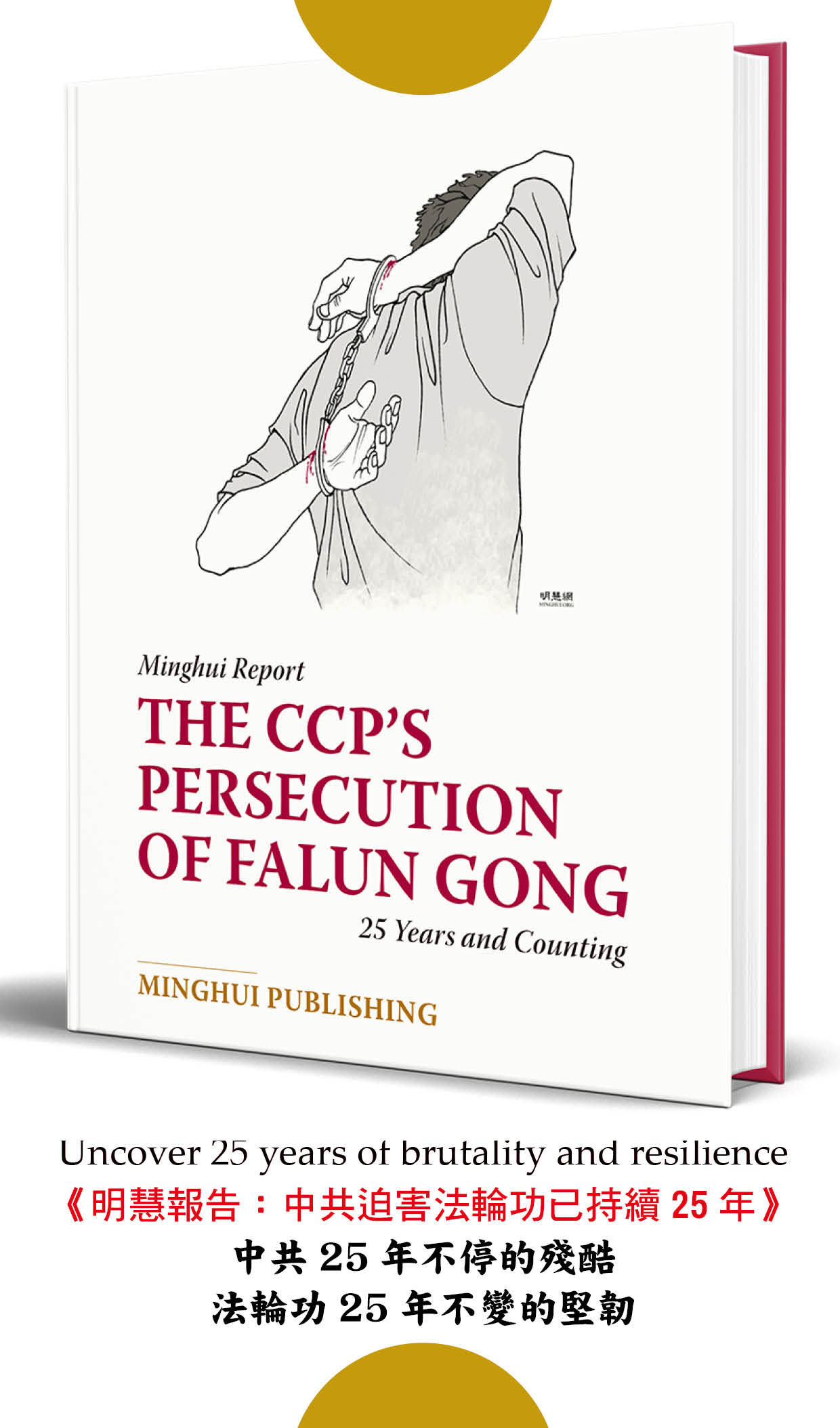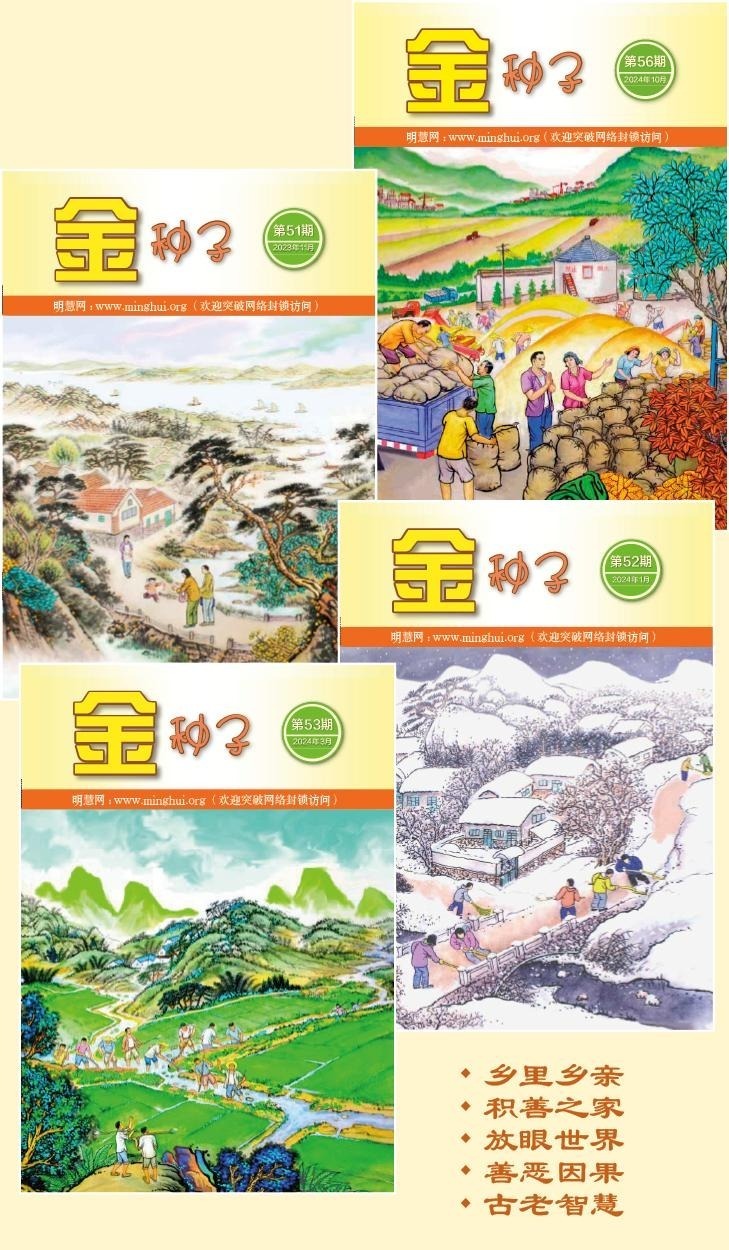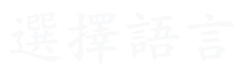法轮功学员夏宁在马三家所遭迫害
——在吊铐毒打中度过两年
以下是夏宁自诉被绑架和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摧残的经过。
两次遭绑架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晚,我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在东街被不明真相的城东小学生举报。城东派出所警察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当晚送到兴城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与关押迫害。
在看守所几天后,城东警察开警车将我送至810医院强制插管灌食。我一直未报姓名和住址。
但在办事处,居委会的人认出了我,知道了我的姓名住址,城东派出所警察将我从看守所用警车拉到城东派出所门前站一会,又将我拉到我住的楼。城东派出所所长、指导员、警察、“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宋长江、居委翟书记,非法撬门抄家。下车后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并告诉警察:生命是你的选择,历史到了最后一刻,珍惜法轮大法就是珍惜生命,善待法轮功学员有福报,善恶有报是天理。
他们等着开锁人来,我一直在喊,他们打开门后就进屋非法抄家,将大法书等拿走,又把我拉回看守所。没过几天,城东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送到马三家劳教所,经马三家医院检查身体,没收我,把我送回家,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则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早晨,我正在家,两名警察跟孩子的爸爸进屋,叫我跟他们走,我拒绝。一个警察拿起法轮功师父的像摔碎玻璃,摔坏镜框,强行把我拖到楼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到城东派出所后强制抽血化验,拍照等。带我出门口上警车,途中我问警察带我去哪,他们说劳教一年。
到马三家劳教所后,恶警张卓慧带我到三大队办公室,大队长张军看了兴城带的资料后说我的劳教期为两年,并说了一些污辱我的很多难听的话。接着他们带我到仓库扒光衣服搜身,将我的左手铐在床上。已经是晚上了,我吃了几口凉饭与咸菜,第二天早上我也吃了几口凉饭与咸菜,心想跟警察讲真相。
开口器撬嘴
早晨上班后,张军、张卓慧进屋恶狠狠地将手铐打开,撸我头发,打我嘴巴,拖我到另一个床上(灌食床),双手铐在床梁上,狠狠打我,还用灌食用的金属开口器想撬开我的嘴。我紧闭着嘴,张嘴就喊“法轮大法好!”到中午了,张军走了,张卓慧还想拿铁器来撬开我的嘴,没撬开,也走了。她们俩狠狠地打了我半天,头发撸掉了很多,我的脸也被打肿了。从那以后我再没吃饭,抗议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几天后,警察强制用开口器灌食。
抻刑
抻刑对人的身体伤害非常大。他们用两个铐子将受害者的左手铐在床梁上抻着,再用布绳子将右手铐狠劲抻很远绑上,这样就使受刑人必须躬身,再把受刑人的双腿绑上,这就造成受刑人的胳膊、手异常酸麻、疼痛。隔一段时间,值班警察将绳子解开,使劲地甩胳膊,说怕残废,受刑人痛得大汗淋漓。
我第一次遭受抻刑折磨在是警察张军、潘玉喜、苑某、潘玉喜下班后,马警察接班,说:张军大队长告诉不要解开手铐甩,拍拍胳膊,那多疼啊。我说你别拍,太疼。张军抻我时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吃,快十二点接班,张军过来,解开手铐,将我站着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我的腿已经肿了,已经到了上半宿,再站着吊铐,那滋味真是痛苦不堪。
第二天早晨张军过来,又使劲地铐上。警察上班后,董彬、张卓慧过来解开手铐甩胳膊,看手腕一层大泡,她俩一看,没法再抻铐,就将我的双手各铐在一个床上边三角铁上。我双手麻、木、疼,尤其右手更麻、更痛,我喊值班警察说明情况,值班警察解开手铐。值班警察走了,来自沈阳的犹大于平作所谓的“四防”,她很配合恶警,我背法她打肿我的脸,豁破我的嘴、脸。她这天很忙,有时过来,有时不过来,我就抽空炼功,一、三、四套功法基本炼完。这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胳膊松快多了,值班警察过来,又将我双手吊铐上,不叫我上厕所,也不许我洗漱。一次我大便憋不住了,喊值班的也不给开铐,我用脚把洗脸盆弄到床上,翘着脚,歪着腰,一点一点脱裤子,接了大便,警察很奇怪我是如何做到的,而我则累得全身是汗。
野蛮灌食和吊铐摧残
我绝食抗议迫害,他们就给我打吊瓶十多天,瓶子打了一麻丝袋子。马三家教养院杨院长,所长周勤亲自参与迫害。一天,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的体重只有九十斤。回来刚进门,他们就将我绑在灌食床上,双手铐在床梁两边,双腿抻绑着,用开口器撑着我的嘴,还围用布绳绑上。恶医护士陈宾将玉米糊隔一会儿灌一点儿,我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弄得衣服、床哪都是。她们下午三点半下班,下班了也不把开口器拿下来,还撑着我的嘴,等他们拿下开口器时,我的上下颌已经合不上了。
晚上他们迫使我站着,将我的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这种摧残整整持续了十三天。
中共奥运期间,迫害加剧,反复遭抻铐、电击、野蛮灌食
当时中共奥运将要开始了,马三家教养院分局派了很多男警察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带队的叫刘永,整天吃着西瓜、桃子和玉米,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搞什么“军训”。出进门要报数、带劳教牌、穿劳教服、唱劳教歌、读背十三条、干劳教活、坐劳教凳,哪一项不配合,都要遭到酷刑:用电棍电、实施抻刑。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没有犯法,而且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所以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劳教犯人,也不配合劳教所警察的迫害。
警察来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分局的人来后,成立个特警队。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把我带到特警队。一天,警察把我带到四楼,刘永和另一个男警察用电棍电我,问我为啥不吃饭,我说我不是劳教犯,我不吃劳教饭。他说你不是劳教犯你是啥? 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俩电了我一阵,把我带到严管办,将我的双手用两个铐子吊铐在床上边,掀我衣服直接电皮肉。
一天早晨,警察把我叫到严管办,屋里都是院、所、管理部门的人,两边床坐满了人。恶警李俊将我双手抻铐在床两边的三角铁上,又将我的眼睛蒙上,迫使我躬下身子,将我的双腿挷上,恶警刘永用电棍电我,屋里警察问我话,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还是象以前那样回答。
又一天早晨,警察再次把我叫到严管办,屋里两边床坐满了院、所、管理科的人,不是上次的人。他们这次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同样象上次那样,他们把我的双手抻铐,双腿绑上,眼睛蒙上,躬身,恶警刘永用电棍电我。
下午五点多钟,他们才给我打开手铐。那时晚上也干活到八、九点多钟。他们下班要走了,刘永问我,你干不干活,我说右手麻,干不了活。他把我带到严管办,将我双手再次抻铐,躬身,双腿绑上,李俊掀衣服用电棍电皮肉,电一阵,打开手铐,解天绑腿,带我回监室。我静坐着,刘永、李俊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他们俩把我带到严管办,再次将我双手抻铐,躬身,双腿绑上,掀衣服用电棍电肉、脖子、脸、腰、手、腿肚子、嘴。当时我大汗淋漓,后来刘永说他们俩一宿没睡。电我、威胁我,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找来记录人,刘永问我唱不唱歌,我说不唱劳教歌,不读、不背三十条,刘永说加期一个月。半夜刘永打开左手铐,甩了甩,第二天早上打开手铐,解开绑腿,让我在屋里走一走,甩甩胳膊,一会儿又将双手抻铐,双腿绑上,躬身。
第二天夜里,我开始恶心,要上厕所,李俊跟刘永说了,刘永说给她解开。我手腕一层大泡,手脱不下裤子,腿蹲不下,慢慢扶墙上完厕所。想在走廊走一会儿,四防人员不让,叫我站着,我回屋,刘永和值班警察正在吃饭。刘永说你回去睡觉去,白天他们干活,叫我站着。我早晨喊法轮大法好,四防告诉严管办人,刘永叫我站着,李俊在走廊里走,稍站不直,他就说。晚上什么时间叫睡觉才能睡觉,记不清站多长时间了。李俊说:试一试电棍有没有电,其他恶警说:我看行。他们借机电我。
强迫灌不明药物、凉水
中共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看电视,刘永说:不给你灌食就吊着你,三天两天给你灌一次。恶医护士陈宾老想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灌药、灌水、捣大蒜水,都是陈宾配合分局干的。分局警察将我和大连法轮功学员杜连英绑在灌食床上,双手铐着,双腿抻绑着,开口器撑着绑上,灌一种红药。这个护士陈宾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教养院、劳教所很出名,她手狠,警察都说,谁能过去陈宾的开口器可不容易。这种红药又辣又不是滋味,陈宾连滴淌在床上的药液都刮下来再给灌上。正常灌食她可不细致,只是几秒钟,不管冷热,不管能不能咽下去,弄得脖子、身上、耳朵哪都是,有时都淌耳朵里去,她可不给擦了。每次灌食不给摘开口器,从她身上丝毫看不到医德医风,毫无人性。
灌了一上午,刚灌完我就全都吐出来了。衣服上、床上都是药,警察只好打开手铐,松开绑腿,脱衣服到外面冲洗。一天他们几个恶警又捣大蒜水灌,又辣又呛嗓子。一天又灌凉水,分局警察拿来矿泉水,护士陈宾不给,换成自来水,一边灌一边拍肚子,肚子胀得鼓鼓的,才停止灌食。灌水不止一次,灌几次。
后来,郑晓丰提出打玉米糊了,劳教人员吃什么就灌什么。那时,我们三个人被灌食,陈宾私自告诉四防人员:不给她灌细粮,菜汤掺玉米饼子捏碎就行。陈宾家里有事就不来灌食了,尤其到了后来,下午多数不来灌食,有的四防和齐春兰知道也不愿意来,为了讨好陈宾,跟陈说不愿意做,陈说:那我下午就不来了。她经常说:饿不死就行。
我被剥光衣服(只剩下裤头)拽到一屋子男警的“特管队”
分局女警察郑晓丰软硬兼施,逼供。我被抻吊时,她经常拿电棍电我,叫我违心做这个,违心做那个,随时电我。一次,郑晓丰扒光我的衣服,我很瘦,三角裤头肥,带松,随时都可能掉下去。她拽我到特管队,而后又到男警察屋,男警察屋里一屋人,走廊里男警察来回走,看到我还说怎么啦?我手紧握床梁,她没拽动。我说你们否认将十八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进男牢房。你今天硬拽我到男警察屋说明什么,这与十八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有什么区别?你把我衣服扒光拿走半个月了,也没拿回来,这说明什么?她无话可说。
分局也采取整天撑着开口器迫害,双手铐上,双腿绑上,陈宾迫害性灌食,放录音。一天分局姓鞠的警察值班,说:夏宁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别把嘴撑那么大了,放点。那天我没遭到罪,
警察用木棒毒打
中共奥运、残运结束,分局警察回去了。中午睡觉我躺着发正念,坐班曲素梅掀褥单,我在结印,值班恶警范国友叫我站着,我结印,范国友拽我到门边,拿大棒子狠狠打我,都打到肋骨上了,按倒我,打我,我喊“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严管办董等人过来,拽手的,拽脚的,几个警察拽我到酷刑屋,把双手抻铐在床的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
晚上睡觉肋骨痛,不能翻身。恶警范国友经常威胁我们,说他不怕扒警服。早上,我在背法,恶警苑国友看到我的嘴在动,就用木棒狠狠地打我的太阳穴,我脑袋“嗡”的一下,没理她,她又狠狠地打我鼻子上,流了不少血,我没理她继续背法,她又狠狠地打在我的嘴唇上,现在还留有痕迹。三棒子打得很重,太阳穴肿了很大的一个包,脸鼻子肿得很大,嘴唇肿了。苑国友出去了,我一直在背法。一个叫潘玉喜的过来,叫屋里人用我的毛巾把血盖上,狠狠踢倒我,还不停地踢踹我。严管董彬过来,带我到严管办,问我情况,让我回屋,我说不回去,他们又把我带到酷刑屋,苑国友经常去威胁我。
一天晚上,值班赵警察说,你回屋睡觉吧,我回屋睡觉,下半夜恶警苑国友值班,夜间上厕所,叫统一去,叫醒我,我上厕所回来,被褥都没了,恶警苑国友给扔了,不叫我睡觉。我躺在床上,苑国友狠狠地薅我的头发到下床,我坐在床上,她又将我头发薅到暖气片上。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几名恶警齐上把我带到锅炉房里,以前我曾被铐过一段时间,到屋里我上牙打下牙,腿也抖,她们俩又给我带到仓库,叫躺下,盖上被子,量了体温,早晨叫醒我,把我带到原屋里。一天所里管理科张警察过来,说你别慌,把情况说明一下,我说明实情,叫他摸摸大包,鼻脸肿得很大,几天后换了杨丽警察,据坐班张雪梅讲,第一棒子好挡着点,不然第一棒子就打死。
恶警用电棍电、抻铐、冷冻、不准上厕所等手段逼我穿劳教服
一天早上,我把劳教服脱了,庞警察值班,她叫我穿上,我不穿,她告诉严管办,董彬叫我穿上,我不穿,董彬用电棍电我,又打手机告诉所管理科。张姓警察(男)来了,董彬把劳教裤给我穿上了一半,叫我自己穿,我不穿,她就用电棍电我,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董彬又电我,我不停地喊,她不停地电,我不喊了,她也不电了。他们用胶带将我的嘴、脸和头发围缠上,带我到酷刑屋,把我双手抻铐在床梁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四天没灌食,第五天灌点稀的,张卓慧把我衣服脱下,硬套上三件劳教服。当时正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他们打开窗户冻我,不给开铐上厕所,裤子尿湿了好几次,鞋也尿湿了好几次,记不清这样折磨了多少天。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警察董彬给我打开手铐,解开绑腿,带我回屋。我的胳膊、腰抬不起来。他们叫我换裤子,洗洗身子。我的手动不了胳膊也动不了,跟坐班曲素梅说,帮助我冲一下,很简单地冲了腿和下身。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不穿劳教服,坐班硬给我套上,严管办张秀云和值班警察把我带到酷刑屋。在这迫害期间,恶警苑国友、潘玉喜把铐子打开,狠劲抻,我的肩膀都给抻过去,重新绑腿,还把腰给绑上。我身体撑不住了,出气都感到困难,我跟下一班警察说给我打开松一会,叫我坐几分钟,她和另一个警察看我实际情况,她们商量打开松一会,坐几分钟,双抻铐上。整天整夜抻铐着,我大声背法。
再遭毒打、反复抻铐
一天夜里,又轮到恶警苑国友和潘玉喜值班,潘玉喜进来拿扫帚狠狠打我臀部,打了好一阵,歇一会儿,又用扫帚把狠狠地打我好一阵,我的臀部被打得青、紫、黑,肿了。张卓慧拿开口器撑我嘴,我紧紧闭着嘴,她没有撑开,我仍被躬身抻铐着,谁踢谁打,都踢在我胸膛和肋骨上。后来我回去睡觉出气费劲,胸膛肋骨胳膊手疼痛不能翻身,穿脱衣服都难,晚上睡觉不让脱劳教服,我脱了衣服,他们连拽带打硬给套上,我的身体因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而时时承受着痛苦,我不得已穿着衣服睡觉,她们又将劳教服缝在我的衣服上。
我天天背法,身体恢复很快,上厕所去水房炼功,我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缝合的劳教服拆开脱下。一天晚上,值班警察杨丽叫我穿上劳教服睡觉,我不穿,她拽我到酷刑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张卓慧过来了,另一个姓苑的警察过来,她们硬把劳教服给我穿上,逼我站着,把我的双手抻吊铐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张卓慧说你可以脱衣服睡觉了。隔一段时间张卓慧又叫室长把劳教服缝我衣服上,我大声背法,她们又把我带到迫害屋,还如同以前一样迫害我。隔一段时间值班的警察来看看我,见我大汗淋淋,打开手铐,解开绑绳,我躺在地上,衣服都湿了,恶警潘玉喜叫我起来躺灌食床上。胡大夫过来,摸摸衣服说,衣服真溻湿了,给我量了血压,灌点食。
一天早晨我起来在床上打坐炼静功,值班恶警潘玉喜过来,拿木棒狠狠打我的背,打一阵子棒子打断了,我没有动。室长叫我穿衣服,坐班(普教)刘某把劳教服套我衣服上了,我扒劳教服,刘某拽着衣服不让扒,我俩争着,结果我被拽到地上了。四防值班警察过来帮坐班,把我拽到酷刑屋,硬套上劳教服,双手抻铐迫害床上。我反迫害,拒绝灌食,并开始讲真相,揭露潘玉喜打我的实际情况,并告诉护士我拒绝灌食的原因。董彬用电棍电我。我的后背被打得肿痛,躺挨灌食床上时更是疼痛难忍。张卓慧过来,我就向她揭露恶警潘玉喜打我的事实。
白天,我天天站着,双手被吊铐在床上,晚间十点多钟回特管队睡觉,早晨三点多钟四防叫我起床,坐班硬给我套上劳教服,拽我到酷刑屋,站着双手再被吊铐,腿脚站肿了。我坐在床横梁铁棍上,臀部坐肿了很疼,我垫上棉袄,臀部的肿痛没有消,后来我垫上褥子,腿脚慢慢自动上来,发正念时腿能自动盘上,悬空着。晚上警察正常六点钟交接班,正好是发正念时间。恶警潘玉喜每次接班看我盘腿,用脚狠狠踹我腿下来,她还就给我双手抻上铐,潘玉喜接班后,不给我打开手铐,十二点半或午夜一点以后才打开手铐。我发正念,她就将我双手上下抻铐,把我的腿也绑上,坐着看着我,还叫四防配合她迫害我。
杨丽看我盘腿发正念,就把我腿用布绑上,手铐打不开了,教养院、劳教所来人谁也打不开,几天了,请示院、所领导用钢锯条拉断铐子。张卓慧说这成了马三家一大新闻了。值班警察刘平看我嘴动,捂我嘴,打我嘴,我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几个警察过来,将我拽到酷刑屋,双手抻铐在迫害床的三角铁上,躬身,双腿绑上,整天不解绳。
经历各种酷刑折磨,我终于脱掉了劳教服直至出狱
二零零九年七月,劳教所将被“特管”的人调到新建楼,说是小号,门电控制,没电打不开,窗外铁丝网。墙里墙外是大地,每个屋子里有厕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特管队”的头子叫潘玉红,她手狠,总打人,值班警察也跟着过来,有看管普犯的警察,恶警苑国友也跟普犯过来,张军跟潘玉红说我干打扫卫生的活,别的活不干。时间到中午十二点了,我坐地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这边警察向跟过来的杨丽等把我拽到另一个屋,双手铐在暖气管上。大队长潘玉红过来说:你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我夜间十二点发正念,潘玉红和恶警苑国友把我拽到办公室,潘玉红叫苑国友拿来劳教服,按倒我。苑国友用脚狠狠踩我脑袋,踩我腿,脑袋踩肿了,腿踩掉很长一条皮,他们打我,扒掉我的衣服,硬给我套上劳教服,将我的双手铐在暖气管上。早晨叫我打扫卫生,我看见我的衣服了,快速脱掉劳教服,穿上自己的衣服,被值班警察发现,又强行脱掉我的衣服,拿走锁起来,给我套上劳教服。
一天我把大麻布围在身上,穿着秋裤,值班警察过来问我,谁给你的秋裤,我说我自己的,他们就硬扒掉我的秋裤,套上劳教服。几名恶警又用电棍电我,还说叫你满地爬,扒掉裤子电腿,电破的地方一年多才好。
我被调到普犯屋里,晚上回特管队睡觉,我脱掉劳教服,借打扫卫生倒垃圾的机会我扔掉劳教服。被非法关押在特管队的法轮功学员都脱掉劳教服。警察上班天天给每个人套上劳教服,她们每个人每天都承受着被电棍电的酷刑。
一天晚上周玉红叫我早点回来睡觉,估计九点多钟。我想今天回来早,我坐下发正念,值班警察见我没睡觉,就去报告,他们掀开我的被子,见我结印,将我拽下床带到办公室,狠狠地打了一个小时,还扎我的眼睛,踢我。我用力喊“大法好”,她们将我按倒,我又站起来,他们又说些污蔑大法的话。警察交接十二点钟,我起来发正念,他们又把我拽下床,拖到黑屋门口,我高喊“大法好,法轮功学员没有罪!”他们就用胶带把嘴脸头发缠上,背铐双手,还按我仰躺着,硌我腰,潘玉红还踩我双脚。过一段时间,他们扯下胶带,把我背铐在暖气上。早上我背法,潘玉红和苑国友又来把我的嘴缠上,交接时,由另外的警察把胶带扯下,打开背铐,带我回屋。我不坐劳教凳,彭涛打我踢我,将我的两手抻铐在暖气上,多长时间记不清了。
又有一次,晚上恶警值班时不让我睡觉,我就说都几点了不让睡觉,他说怕你脱劳教服,如果你保证不脱就让睡觉。我说什么也不答应,我拿褥子回那屋躺下,等他出去我就把劳教服脱了,后来被发现,他们把窗户门都打开让蚊子咬,屋里墙壁飞满各种昆虫,蛾子,蚊子,但蚊子没咬我。
我知道锦州法轮功学员徐慧胳膊骨头拧着,疼得天天哭,是恶警潘玉喜拧抻造成的,并且不让别的同修给她拿行李。我每天十二点钟发正念,男女恶警都来打我踢我踹我,还告诉值班警察我发正念扣他们工资。就这样,每天只要是背法,发正念,不穿劳教服,就是被迫害,被电棍电,被踢被踹,被背铐。
二零零九年十月,又将我从特管队调回三大队,值班警察跟过来,普犯警察也跟过来,潘玉红及办公室的警察也过来了,张军,张卓慧,张秀云给我带到仓库,站着双手吊铐在床的上边。几天后,值班警察给我吊铐到另一个床上,挨着我被吊铐的床堆些被子褥子,我脚蹬上床,用脚勾来褥子垫起来坐上,能自动盘腿发正念,被他们发现后,把褥子拿走,趁我出去灌食的时间,把我床上的东西全部拿走。
值班警察刘平很邪恶,告诉四防看我起来就叫她,拽我下床,打我、踢我。潘玉红看我回屋背法,就捏我嘴,按倒我踢踹我,还叫刘平帮她,把我的双手背铐在暖气片上。早晨起来,硬给我套上劳教服,双手吊铐,我趁开铐灌食机会,一边走一边脱劳教服或者灌食起来马上脱掉劳教服,护士和警察硬给我套上。值班警察把劳教服缝在我衣服上,我跷脚拆掉缝线,拽领子从头上往下扒到两边胳膊上,警察开铐,快速脱掉劳教服。
持续很长时间,终于脱掉了劳教服,他们再也不给我套了,直到走出劳教所。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1/3/22/1239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