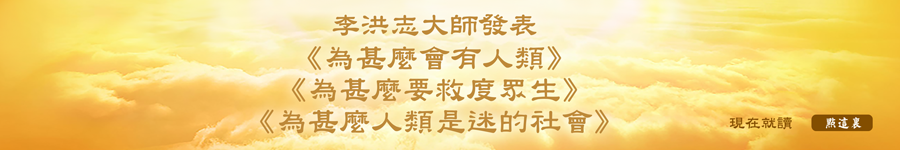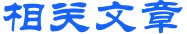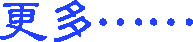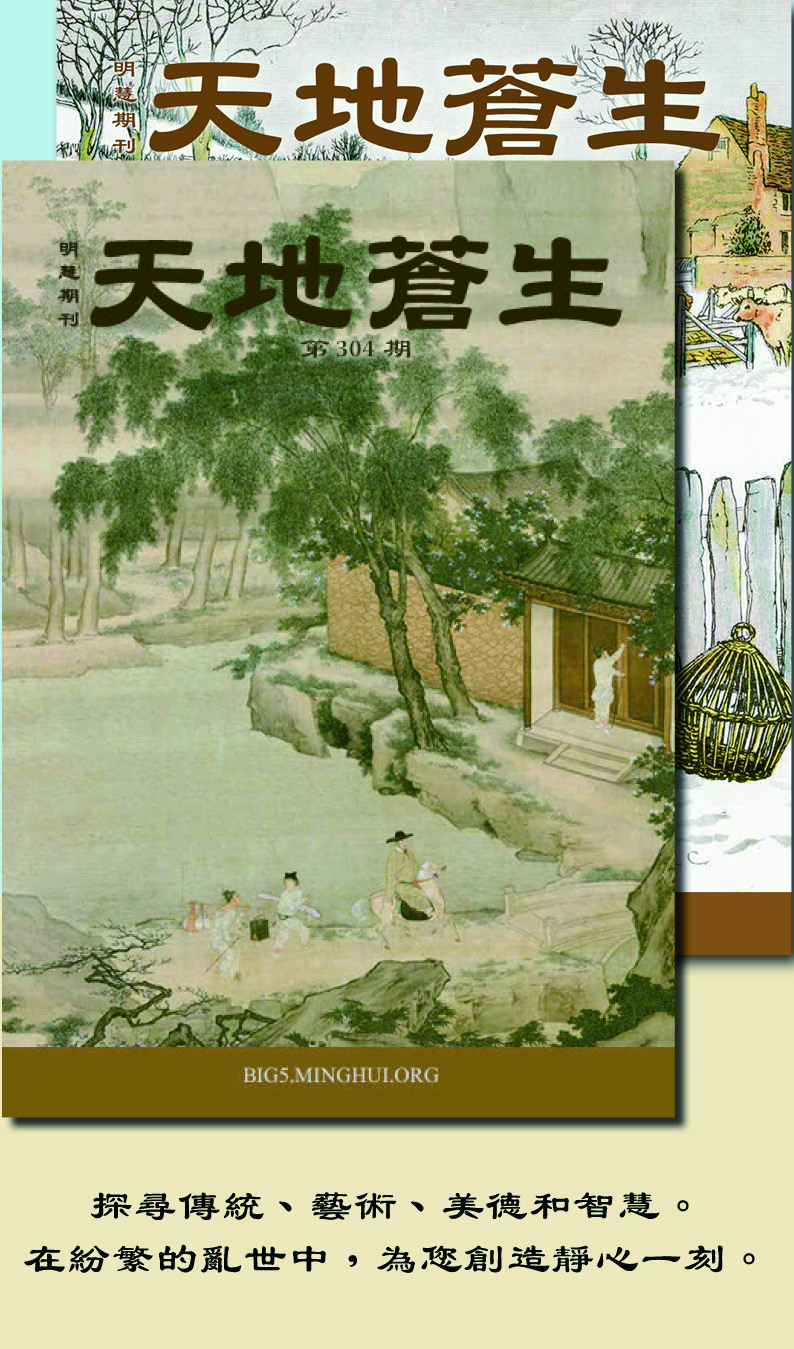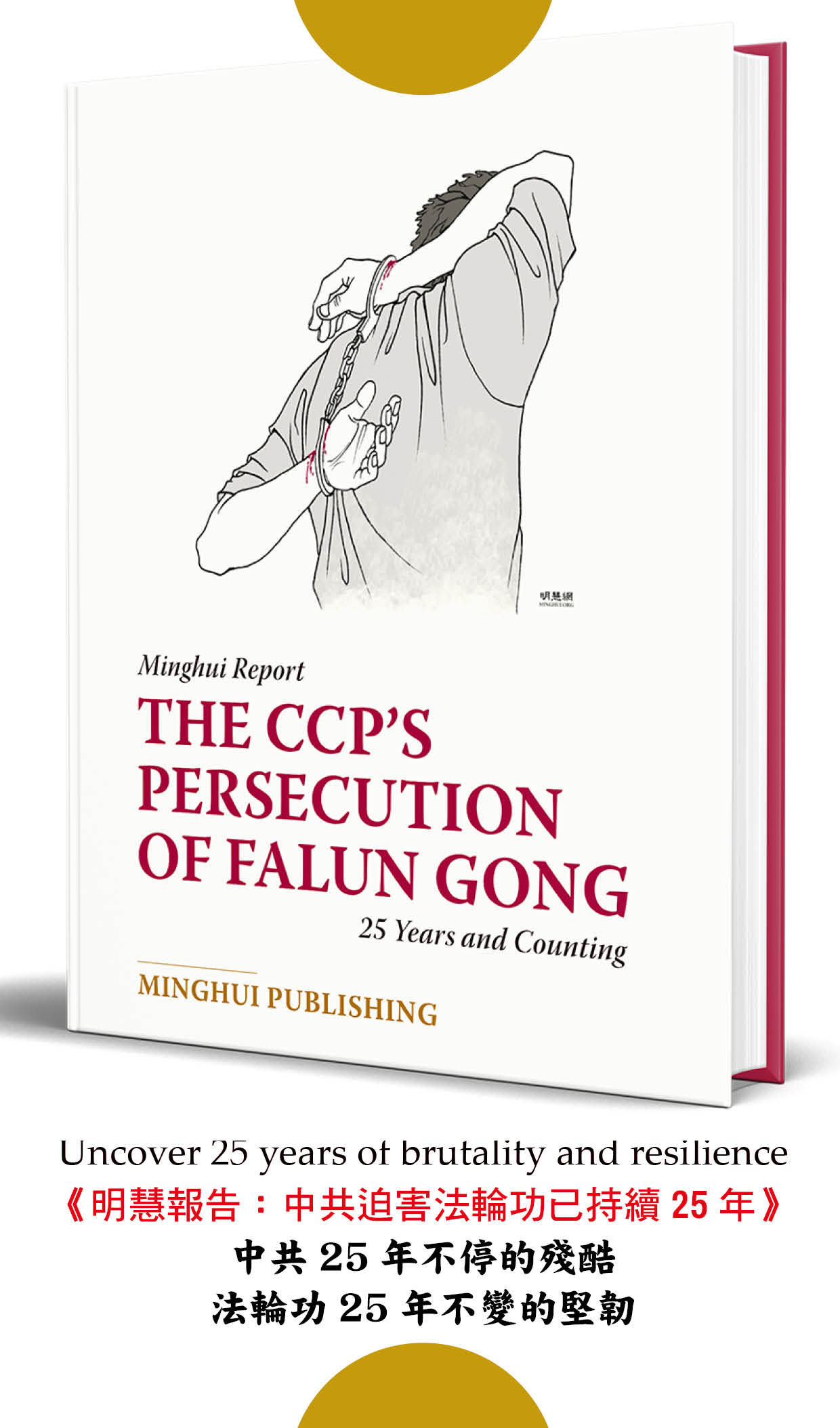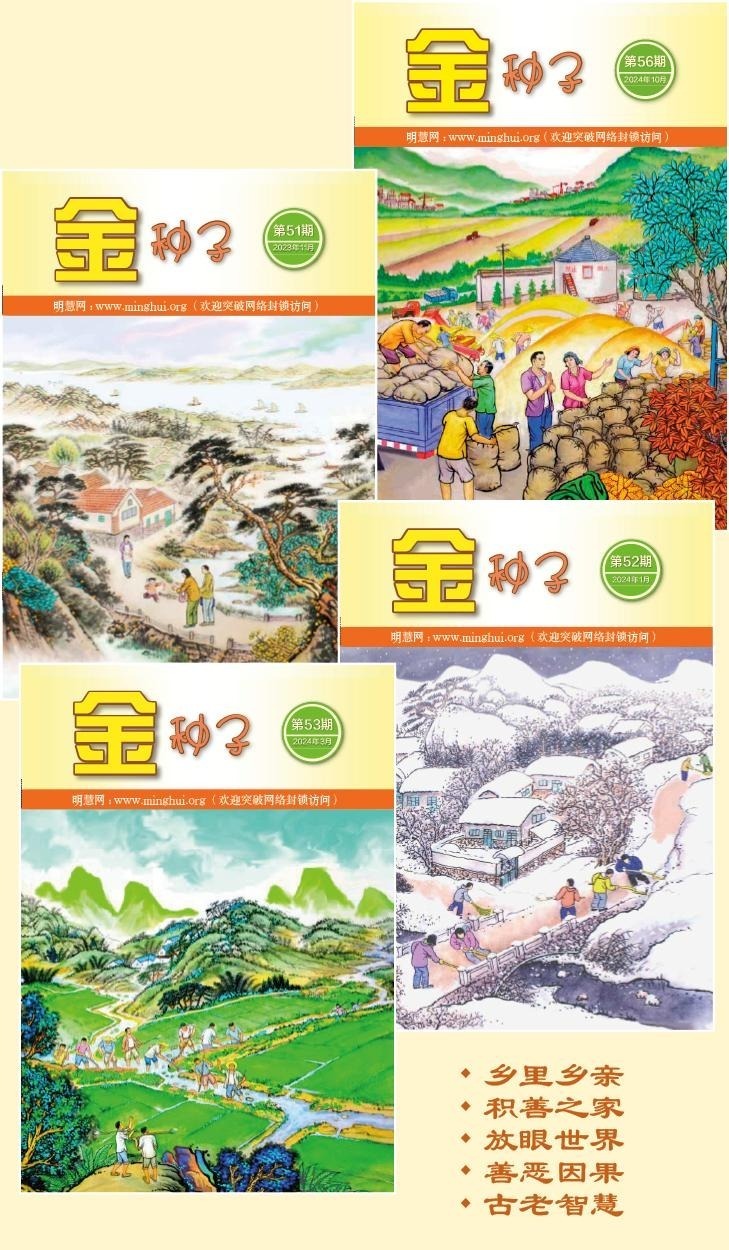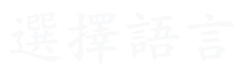盘锦教养院的非人酷刑无法动摇我坚定的信仰
1999年7月,江氏集团公开诬陷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为给大法讨个公道,我去北京上访。2000年2月,我再次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拘留2个月。2001年2月,我向我住地的居委会主任讲真象,劝说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却被其举报,我再次被非法拘留2个月。由于我拒绝所谓的“转化”,他们非法判我劳教一年。直接把我送进了邪恶的盘锦市劳动教养院。
在教养院由于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配合恶警们的指令,2001年4月19日晚,恶警们扒下我的棉衣,把我吊铐在铁栏门的迎风处,凛冽的北风吹得我浑身冰冷僵硬、手脚麻木,直到后半夜它们才把我放下。第二天又把我铐在窗栏上。它们见吊铐也未能使我屈服,就从5月20日起逼我蹲在地上,每天蹲到后半夜,到22、23日,连续蹲了2天2夜不让睡觉。到25日,我实在蹲不了了,它们就逼我从早上5点跪到晚上5点,晚5点后逼我双手抱头蹲马步。
它们见一周的折磨仍不能削弱我对大法的正信,就在教养院副院长张守江的指挥下,对我实施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方案。25日晚7点,恶警齐霞将我带到楼下的一个小黑屋里,恶警刘静、蔡丽等在里面。我一进去,她们仨就开始攻击、污蔑大法,我告诉她们:“诬陷大法是有罪的。”她们闻言便就发疯似的用手打我的脸,一个人打累了换另外一个人,直到她们的手都打红肿了,然后换上狼牙棒接着打,直到打得她们三人都累得喘不上气来才停手。这时的我,从后背到臀部伤痕连成了一片;左肩膀被打坏了;右手失去了知觉;胸内剧烈疼痛,汗流如注,汗水流入伤口,更是钻心。即使这样恶警们仍然不依不饶,让我回去继续蹲马步。当晚11点左右,我又被恶警齐霞带入那个小黑屋,进屋后发现邪恶阵势大增,大队长羿秀艳、恶警黄亮、蔡丽、赵红艳、刘静等凶神恶煞般地等在那里,羿秀艳拿着笔歇斯底里地嚎道:“这回非叫你‘化了’不可!”看到这阵势、听到这嚎叫,我心里明白:更大的考验来了。没容我多想,这群兽一样的东西就“嗷”地一声扑了上来,这个打累了换那个,每个都在争当最狠的打手。都打累了就换上了狼牙棒。在它们眼中,我就是个沙袋,它们车轮式地全力攻击。我想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毫无顾忌地下死手,就是看透了我没有丈夫,即使把我打死,我弱小的女儿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它们叫嚣要“化了”我的动力吧。
我——一个弱小的女子,它们不相信“转化”不了我。这就是它们的无知。我想起了师尊《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的“修炼者坚定的正念超越一切人的认识,超越一切人心,是常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同时也无法被常人改变,因为人是改变不了觉者的。”
它们见我仍没有出现它们所希望的状态,就兽性大发,她们扒光了我的衣服,疯了似的扑上来,用手撕掐我全身皮肉,已经严重损伤的皮肉经她们恶狼一样狠命的撕掐,一下就破了。哪一块皮肉不连着心啊!破皮的地方即使不碰也疼得钻心啊,可她们却专在破皮的地方下死手。我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楞是一声没吭。这些恶魔现出了本性:一面折磨我,一面变态地哈哈大笑,用别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为自己取乐。她们是人吗?我认真地看了看她们,发现她们的脸真的变形了。尽管她们给我制造了那样大的痛苦,但我内心中却觉得她们太可怜了,仅仅为了“转化”大法弟子的那点奖金,就真把自己变成了恶魔,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她们却一无所知。
恶警头子羿秀艳见我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了,就说:“算了吧。”恶警刘静狂笑着说:“我还没掐够呢。”6个恶警直到筋疲力尽才停手。接着她们把我带出来审问,一个支持不住就换另一个,六个恶警轮着上,我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她们却不让我闭眼。
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我内脏受重伤,第二天早上大口大口吐血,第三天开始便血。同室的人见失血量很大就向教养院反映,教养院却不当回事。便血持续了3天3夜,吐血持续了11天,血量才有所减少。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师尊保护,我这条命真的早就会被这群恶魔给“化了”。
恶警们见我身体稍有好转,便迫不及待地再次下手了。2001年6月29日晚12点,恶警柳敏、赵红艳将我一只手铐在窗栏杆上,另一只手铐在地面水暖管线上,这种斜铐的酷刑使受刑者站不了又蹲不下。由于我内外伤仍很严重,铐上后不到一分钟就疼得冒汗了。到后半夜2点,我呼吸极为困难,恶警怕出人命,才将我放下来,放下后我一头就倒在地上,很长时间才缓过气来。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恶警们竟然让我爬回了房间!回房后我仅仅喘息了2个小时,它们又开始了折磨,逼我抱头蹲在地上转圈走。
在盘锦教养院,它们对付坚定的大法弟子的酷刑有20多种。
对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它们使尽了招术却仍没“化了”我,我还怕它们什么?于是从2002年2月1日起,我开始公开在盘锦教养院炼功。恶警羿秀艳、刘静发现后将我毒打一阵,然后逼我蹲马步。还扬言要加刑。2月2日,我正炼功时恶警黄亮将我一只手吊铐在暖气管子上,她走后,我继续打坐到天亮。从这天开始,无论白天晚上,它们都把我铐在那里不放下来。
由于长期的酷刑折磨,大量失血和内脏损伤,我已经皮包骨了,别人都说我变形了。生命的迹象仅仅是微弱的呼吸和心跳。残忍的教养院也发现我的状态不对了,它们不想承担“酷刑致死”的责任,就强行把我送到盘锦市第一医院,检查后大夫告诉它们:“要立即住院治疗,住了院也有生命危险。”我拒绝住院。
教养院见硬的不行,又想出了软招,动员我的亲属来做工作。失去了生活唯一依靠的女儿见我被折磨成了那样,料想我难以活着回家了,孩子扎心似的放声大哭。我识破了它们的企图,硬是让它破产了。心想软的它们也休想得逞,我悄悄告诉女儿:“你不要哭。”仅三天时间,我就奇迹般地恢复得红光满面了。恶警们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
邪恶的盘锦教养院没能“化了”我,它们也不可能“化了”我。我闯过了生死关,堂堂正正从盘锦教养院闯出来了。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3/6/15/369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