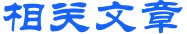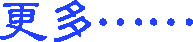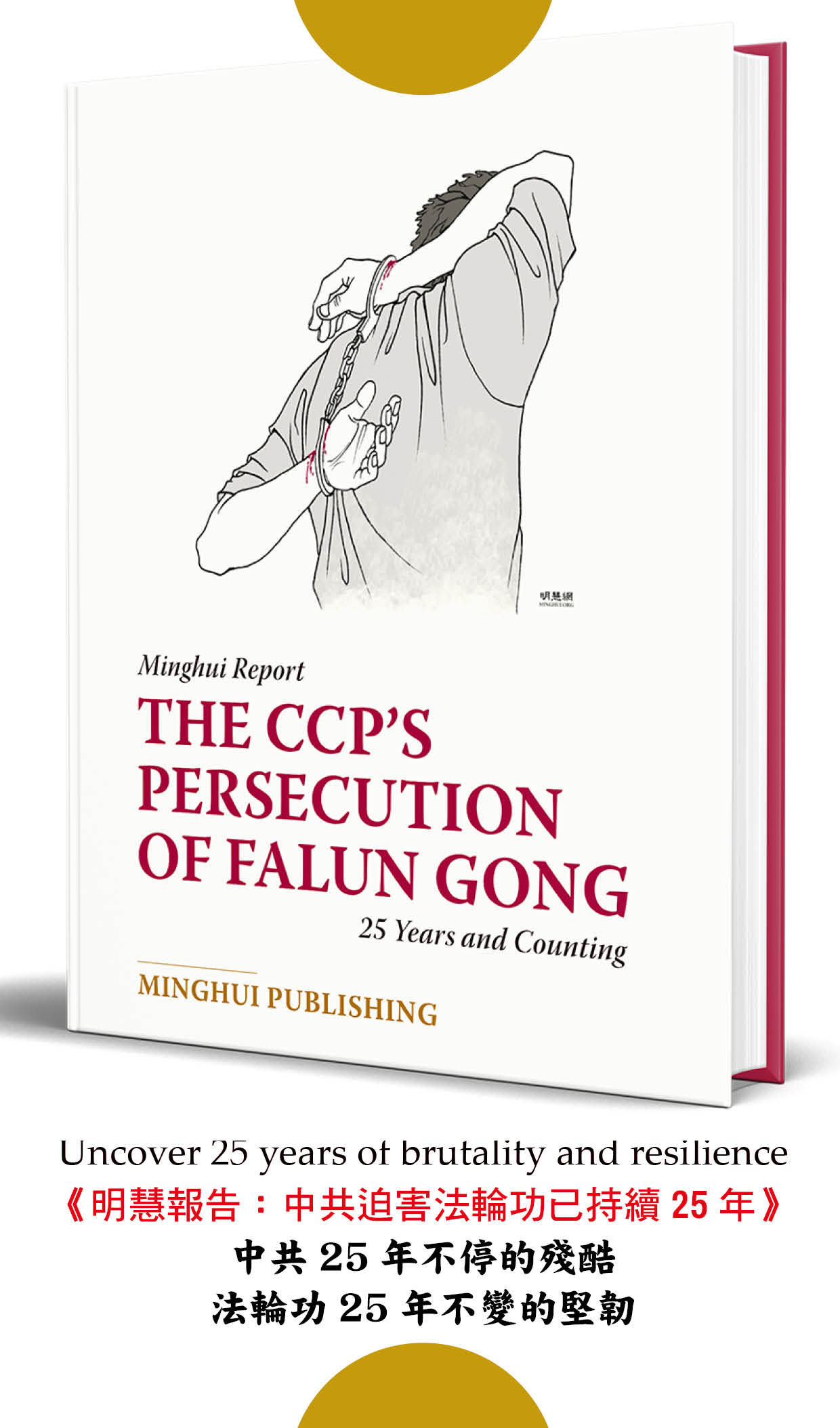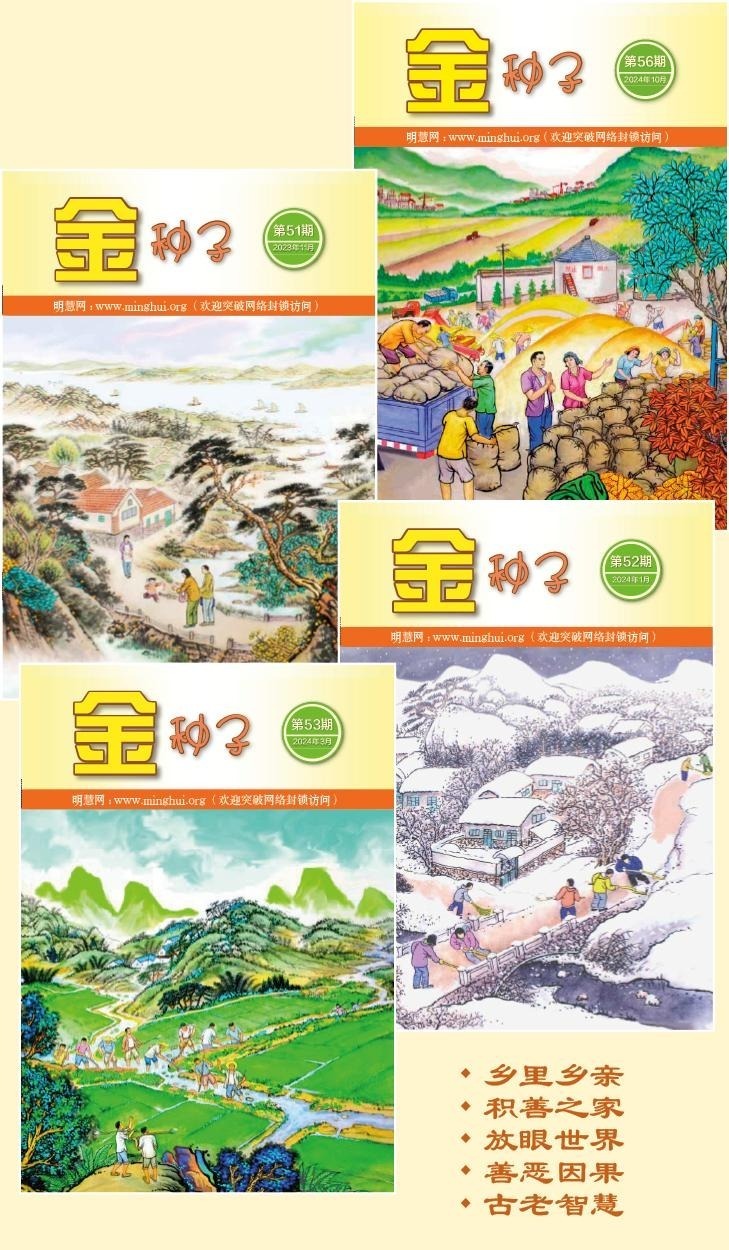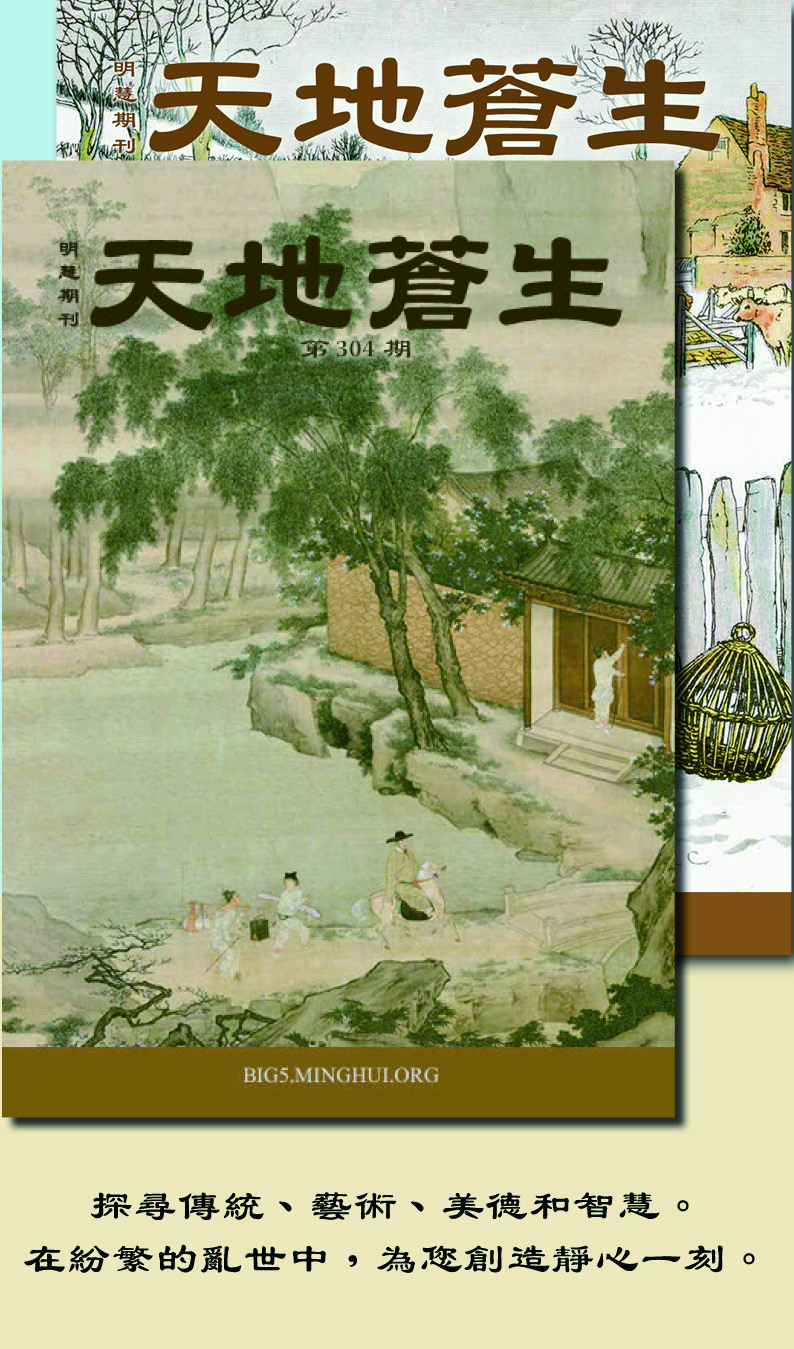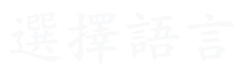用正念营救我们的同修(译文)
蒂娜:
我叫蒂娜,家住德国北部。在一次地区性的交流会中,一个同修提到了师父针对营救学员所说过的话,这时我才明白参加援救在押的同修的重要性。在2003年元宵节美国西部法会上师父说:“你们的同修大法弟子一定要救,不能被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其实呀我告诉大家,迫害大法的一切做法都是最愚蠢的,你们回想回想都是这样,因为旧势力就是那样安排的。”(《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在做营救大法弟子的音乐光碟的10个月中,经过了不少磕磕碰碰。整个过程中我最大的体悟就是修炼中一定要放下各种执著和同修之间相互配合是关键。
凯洛林娜:
我叫凯洛林娜,来自德国海德堡。我在营救学员的活动初期所参加的在德国南部的为期8天、以波恩中国领事馆为目的地的紧急营救自行车之旅,是给我体验最深的一次行动。我感受到一种表现我们的意愿的力量。这是一种来自于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力量,是因为被允许为大法付出才能体会到的力量。
但是,我那时做这些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营救熊伟吗?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借营救之事避免直接与常人讨论法轮功。这真是个很奇怪的想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对法的坚信啊? 然而事实上的确有东西阻碍我同化真善忍。那就是一些旧的观念,特别是对自己的执著。自私引发出了对自己的怀疑。象其他同修一样,我当然想为援救熊伟助一臂之力,然而我是带着怎样的心呢?周围的环境常常反映出自己思想中的漏,我应该认识到不足并且改变它。
克里斯汀娜:
我叫克里斯汀娜,来自德国南部。在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学员。我尽可能增强和其他地区同修的交流并由此开始投入营救的组织工作。在正法中,共同交流,相互协调与沟通是一个体现正法行进和步骤重要方面。圆融好这个整体并且发挥他的巨大能力可以遏制破坏法的邪恶。
开始时尽管我知道这场镇压的邪恶,但是内心深处总是感觉到一定的距离,没有那种切肤之痛。我对这种状态很不满意,所以决定要在自己和营救熊伟这件事之间建立一个感性的联系。一个受过酷刑迫害的弟子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年会上讲述了她所经受的种种折磨。为了对那种痛苦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和体会,我去旁听了几次。
我发现,我多了一些慈悲心,这帮助我更好地给媒体和常人讲真相。有了遭受迫害的感同身受,营救的紧迫感就强烈起来,于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目标清楚而集中的营救小组随即产生。通过整体中的相互配合, 共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提高。每个大法弟子都更加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这一特殊时期所负的重大使命,也越来越成熟。对于具体营救行动所出的主意不断地得到实行。
蒂娜:
从很多方面我认识到我们那些不好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正法进程。我也一再发现自己常常是用人的思维在看问题。比如说我丈夫用音乐方式参与正法,我不懂音乐,只能被动地参与那些工作,心里不高兴,我想要走自己的路。我的丈夫在音乐室里时,我得在家带孩子; 他去演出,我得在两个儿童床之间忙来跑去。
碰到争执或矛盾,我们的口头禅常常是:“看看你自己吧。”在正法活动中一碰到问题,我就想“他就从来不看自己。” 现在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在滥用法理了。当一个人批评别人不向内找时,他就已经是在向外找了。
凯洛林娜:
一天早晨正当一位女教授走过我身边时,我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有很多学生参加的聚会上为营救征集签名。她的态度很生硬,摇了摇头,其实她对这件事不太了解。我很沮丧,心想她根本还没有听我解释,怎么就拒绝了呢?我有些生气了,对她有些不屑。其实是因为自己个人利益受到了伤害才感到不平。比如“她对我的印象一定不好了”,或是“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考试?”这时候我是既没有善,也没有忍。我发现了自己怕被拒绝的心。
而且我还发现对自己产生的怀疑,会引起别人对我也产生怀疑。那天在我摆放在大学里的征签表上赫然写着:“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是一个点化,叫我无论是在营救的过程中还是自己的修炼都要更加坚定和坦荡,我想起师父说过的话:“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
克里斯汀娜:
我在做大法工作时,常常会问自己,这会不会有用,是否会被人们重视。有一次一本杂志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就期待会有更多的人在网上为呼吁营救而签名。现在我懂了,这不在于我去指望常人会为我们具体做些什么,因为我还不能知道他们拿了资料后内心会有什么改变。回头看我自己的修炼过程,难道我不也是花一定的时间以后才积极行动起来的吗?现在对待那些要救度的生命需要同样的包容。
同时我也看清了,我们所做的都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在另外空间发挥他的作用,会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中被看到。这一切都有他的主线,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兑现着他的誓约。
蒂娜:
后来,我读了一段师父的讲法: “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
我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心里觉得不平衡,因为我一直好与别人争执,难以合作。而恰好在正法活动的时候,我们合作得不好,师父的这段话使我看到了这些要修的东西,不再执著自我感受,固执己见。想起曾经和我丈夫因为这张CD而争吵时,我今天还觉得惭愧。
我们的矛盾从为一首歌写歌词时就开始了,我丈夫想要我写一首歌词,但我想为正法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我有被命令的感觉。相应的,这首歌词总也写不好,随之而来的批评我也不愿接受。直到几个月后,我们两个才能够合作。他接受了最后的版本,经过进一步的修改,这首歌词完成了。
同修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不要期待对方能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至少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真正地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看待。
卡罗林娜: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投入地往中国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常常同时放那首歌曲,有时也向他们播送起诉首恶的广播录音。一般我采用对方比较能够接受方式,传给他们相应的内容。有时对方在电话的另一端谩骂,我就再给他打一次电话,向他播放“得度”那首歌曲,直至他安静下来注意地听。
有一天,我的录音机突然不转了。我试着向内找,可是找到的都是外部原因。当然,我可以在没有录音播放的情况下继续打电话,可是那样的话我就得自己说,所以就没有继续打。很快,我就发现,我太倚赖什么了,成了一种惯性,这又是一种执著。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录音机又可以用了。
克里斯汀娜:
当我遇到在以色列生活的熊伟的哥哥时,我们马上想到一起合作一个项目:一个为了营救的德国-以色列电话周。当一组学员发正念和学法时,另一组学员给劳教所和有关负责部门打电话。在这一周里每天早上就开始打了。
我们把重点放在营救上,但也顾及到了别的方面,如对邪恶之首的控告,一些明慧网中发表的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通过大法弟子这样密集的打电话,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受到了很大的震慑,因为它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们害怕曝光。
当然一些个人的障碍,如怕心、争斗心、觉得自己不会中文和英语而无法打电话等观念,每个弟子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些执著,去掉它以后,才敢打电话。以前很多学员有想给中国打电话的愿望,但他们没有能够把这些障碍去掉。通过这样一起打电话的约定,我们感觉到了无法推卸的责任感,那些障碍消失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每次我拿起话筒,我的心还在跳,但我的怕心越来越小,我越来越平静,甚至我可以直接和一个远在中国的,等待救度的人对话。同时我也在做的过程中学习到,如何更好地利用我的和别人交流的能力。
有时为了表达对我的感谢,听电话的人会问我他能做什么。一次当我和一个军人长时间通话后,我想到,除了讲真相,我还可以和他谈一些常人方面的事情,如家庭、朋友、生活方式、旅行和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等等,这样他也会从人的一面了解并尊敬一个另一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蒂娜:
在电话周里,我没能如所计划的那样与其他同修一起在早上打电话,因为我在这个时间里总得照看孩子;另外,我感到连续一个小时发正念很困难,因为,我连十五分钟发正念都很难保持精神集中。于是我把往中国打电话的时间安排在清早两点到三点,并且时时保持正念。
当我打电话时,我想着如何冲破那些导致对方不能注意听我讲话的干扰。我尽力排除自己的所有敌视在劳教所和劳教部门工作的常人们的念头,试想着他们也是父亲、母亲,我把他们当成朋友。这一晚上的电话几乎次次成功。他们倾听了我的讲话,有人还愿意帮助我,用他那断断续续的英语告诉我其他人的电话。我被此经历震撼了,这一经历让我清楚看到了坚定的正念是有多么大的威力。
卡罗林娜:
不管我走在哪里,我总是想着中国。我有些明信片,是专门寄往关押德国学员的劳教所的。师父说,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讲真相的对象。不管我买东西也好,还是在火车上、邮局里,或是在街上散发,人们都很愿意接过这样一张“为了人权的明信片”。
通过这些营救活动,我们反过来利用邪恶的这场安排,揭露和除掉各种藏在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样才能使人们能够认识它们。假如熊伟释放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讲真相的好环境,并且进一步用智慧使人们认清这场邪恶的迫害,认清它在此特殊时间里是如何针对大法犯罪的。
克丽斯蒂娜:
通过对熊伟的命运的关注,不只在常人中,而且在我,一个修炼者的心里,一扇门打开了,中国发生的事情被推到了我的眼前。那种在情的基础上的,只是对少数人的善,变成了对众生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谢谢大家!
(11月23日柏林法会发言稿)